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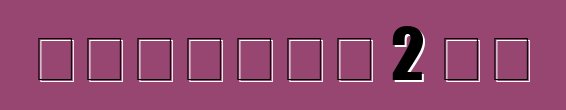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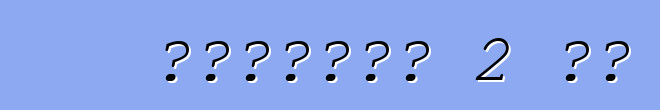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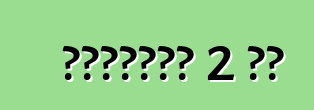
是还是不是?
再次,愤怒的曼陀罗。它不应该被忽视,特别是如果另一个恶魔悄悄出现在关于吃什么的争论中。在正常的曼陀罗(反映创造物质世界和微妙世界的能量相互作用的佛教宇宙图)中,能量顺时针移动,空气激发灵感,火支持欲望,地球计划如何获得它喜欢的东西,水选择最好的过程行动。在愤怒的风中,它吹向水而不是火,这就是为什么嫉妒的头脑在了解到存在比它自己的地方更好的地方时,会掀起风暴并呼吁与不公正作斗争。如果你幸运地到达岸边,你稍后会收集常识的碎片。因此,萨满教的武库中有如此多的惩罚,改善的途径在于抑制冲动,将愤怒、怨恨和嫉妒的能量用于和平目的。为了让一个人学会如何控制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萨满教的天堂慷慨地在他的头上倾注了一些情况,让受苦的人放弃社会引起的幻觉,并笑着面对自己的恐惧。疾病、失败、拒绝、绝望在这个系统中看起来是净化灵魂的最佳方式。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正文:“萨满被敦促变得非常生气,并以笑声化解他的愤怒,首先是对他自己……精神的吸引力可能会让人感到羞辱……因此,通常,萨满的信仰是决定于他可以多么大胆地诅咒天堂,因为他们给他的礼物。对上帝的爱实际上是萨满生命中唯一让他有理由活下去的力量。亵渎常常是他唯一的祈祷。在这个悖论的严酷考验中,在失望的炭火上,在愤怒的熊熊烈火中,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之刃诞生并被锻造,对人们所谓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冷漠冷漠。
查拉图斯特拉通过尼采说的大致相同,但这位萨满哲学家似乎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他。 “小品”中有如此多的悲情和激情,你可以像向女武神开炮一样发射它们。但另一方面,当你跳出悲惨的丛林,屏住呼吸后,你得出的结论是作者基本上是对的。在本质上,在图瓦的核心,隐藏着冰和狂犬病的混合物。这种元素的致命作用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对比,从骆驼和驯鹿的邻居到最严重的社会退化与莫斯科相当大的财政注入的结合。这里的人民和当局在荒谬的日常实践中团结一致:我记得我在某个地区假期在当地电视上看到的一篇报道,当地的劳动英雄骨瘦如柴,包括几名牧羊人、医生和不可避免的官员,沿着尘土飞扬的广场漫步。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张男孩的照片,他在 9 月 1 日之前,吹着玩具口琴,试图挣钱买校服。我读了一个关于非常便宜的棺材的广告,然后我读了一篇关于当地官僚氏族秘密战争的分析。没错——这里的生活在边缘情况的剃刀上跳舞。也许即使是点击一下也能将一大群厚颜无耻的塔巴甘人扔进垃圾桶,他们穿着昂贵的夹克,上面有副徽章。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更容易:白天,一个被扔石头的司机可以在晚上撞倒 - 杀死笨蛋,手机,甚至那样。
这里的一切都是矛盾的,一切都使感官敏锐。当一般的“公共”现实有时似乎像故障电视上的图片一样波动时,你甚至不会感到惊讶。要么你突然发现自己的感知被分成几股,要么你觉得通常的等级制度像沙子一样崩塌。但从上面看,这种日常的挑衅被一部和平的佛教沉思电影所覆盖。
不合时宜的想法
- 娜塔莎,你玩 dung-u-r 吗?当我们前往克孜勒附近的 arzhaan(春天)时,Ken Haider 问道。
Dungur是萨满的手鼓,我当然没有,Ken有,而且上面覆盖着羚羊皮。肯和他永远的同伴人类学家蒂姆霍奇金森是两个被图瓦抓获的英国人。肯是一个高大、肥胖的人,他是一名萨满祭司,也是 Tash-ool Buuevich Kung 的第一个学生。他们是由图瓦“萨满师”指挥官 R. Kenin-Lobsan 在 90 年代初引入的,当时 Kunga 正在他的家乡萨马加尔泰村亲手建造一座 khuree(佛教寺庙)。 Kenin-Lobsan 带了一位外国游客去见一位当地的爱好者。然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狂热者在英国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迹象,肯作为萨满离开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与图瓦正在创造的狂欢相反,当钻石所有者像蝗虫一样繁殖时,最主要的不是礼物的存在,而是对萨满工会的贡献,来自天堂的真正祝福是独一无二,因为聪明的人才在任何人类领域都是独一无二的。
Ken 的战斗就像他的九次红色 menges - 它们看起来像是短暂而激烈的较量。难不成,鬼魂们也像掠食动物一样,在同样凶猛的攻击下附体了肯恩?门格(痣)——在藏蒙占星术中,与西方黄道十二宫的星座相同,是一个人的基本星座。一位经验丰富的祖尔卡奇占星师从中提取了深渊的信息,但即使对于像这些台词的作者这样的完全外行,也很明显,九个红色门格的主人有很多火。这是一个意志坚强,浮躁直率的人,天生的领导者。
在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 arzhaan(来源)附近,距离 Kyzyl 不远,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时间拿起相机。 Tash-ool Buuevich 在火上点燃了一根北京杜松的树枝,并敲响了某种狡猾的双铃。肯抓起一个手鼓,开始像敲鼓一样敲打它:
-地球!大地之母……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如此有力量,以至于永远嘈杂的树木都安静了下来。这就是一切结束的地方。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目标 - 离大 ov 不远的一块空地 - 显然是一个永久性的礼拜场所。周围树木的树枝上挂着感恩的柯达围巾,通常作为对灵魂和人的尊重的标志。在这里第一次有可能看到 T.B. Kunga in vests,对于他级别的萨满来说,他的 manchak 非常简单,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顺便说一下,Ken 有一套苦行服,T.B. 的其他学生。它们一般看起来像黑袍僧人,但阴阳图是一样的。在这里,Tash-ool Buuevich 与 Ken 的手鼓一起工作,并说出他的“maralukha nada,maralukha!”。然后蒂姆将手鼓翻过来,向这些诗句的作者解释萨满宇宙是如何运作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三个地址——山区的arzhaan,车子在一条肮脏的危险道路上爬行了很长时间。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牧羊人,在这里肯在我头上敲响了他的手鼓。现在很清楚当他们用敲击器敲打地毯时的感觉,但那时候感觉很简单也很好,就好像一年来积累的所有污垢都被打掉了。山中的阿尔扎安不仅神圣,而且疗愈。山上有专门的营房,图瓦人夏天全家住在里面,用当地的水处理。他们说一周的课程持续到明年。在回来的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想法:图瓦的土地让一些人感到愤怒,让另一些人感到谦卑,而一个小共和国的天空,其美丽无情,似乎以超乎人类感知的超高频率振动。显然,巫师是神圣意义的解码器和外来能量的转化器。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了一个顽固的酒鬼或很快死去——能量太硬了。
时光机
事实证明,奇迹不仅仅存在于图瓦。第二次旅行后,我就被塞进了一个采访中,虽然英语说俄语一般,而且这些台词的作者有五岁孩子水平的英语词汇量。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包括困难的事情。 Tim 和 Ken 第一次来到俄罗斯是在 80 年代后期,他们在一个大型摇滚音乐节上掀起了改革浪潮。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一起进行了带有民族主题的即兴创作,Ken 当然会打鼓,而 Tim 的遗产是电子、萨克斯管、单簧管和弦乐。早在图瓦,共和国人民艺术家、著名音乐家 Gendos Chamzyrin(手鼓和喉咙歌唱)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英国人第二次被带到新西伯利亚市,他们应该在大学校园里表演。有些东西在组织上没有共同成长,为了提高对外国人的期望,决定展示当地的好奇心。于是流浪的音乐家们来到了尼古拉·科济列夫的铝镜前,因为当时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V.Kaznacheev指导下的临床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实验正在镇上进行。目的是检验天体物理学家 Kozyrev 关于在特殊凹面镜中压缩时间的想法。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科济列夫 (Nikolai Kozyrev) 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是官方科学的贱民,“真正的”科学家在他背后嘶嘶作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科济列夫思考了时间的本质及其与能量的相互作用。他提出天体是能量生产机器,时间是加工原料的理论。时间,从而成为保证宇宙生命得以维持的物理过程,它可以以不同的速度流动,可以延缓,可以压缩等等。蒂姆同志和肯同志面对未知毫不退缩,大胆地爬进实验镜 - 铝制眼镜,由折叠成一圈半的板制成,里面有椅子和设备。
然后媒体写道,实验参与者飞向过去,一些飞向未来,据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迅速而悲惨地死去。但蒂姆和肯还活着,他们活得很好,他们在一个难得的世界里,他们扮演着纯粹的另类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乐趣。他们找到了第三个 - Gendos 并创建了组“K-space”(“Kozyrev-cosmos”),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找到并收听。再一次,肯遇到了一位老师并成为了一名巫师。根据蒂姆的说法,科济列夫的镜子只是让他们回到了童年,他们从小回到了童年,成为非常快乐的人。
库哲格峡
顺便说一句,在原始人的古老观点中,也有一种时间流逝不同的假设。例如,地球的时间比火的时间慢得多,东方占星术的预测就是基于这个特性。但是从原始民族那里得到什么呢?科学界追赶他们并不是为了将他们归入斯大林主义阵营,也不是为了无礼地将他们从他们最喜欢的工作中解雇。
而我们的时间无情地飞到终点。它紧贴着灰色的沥青路面,黑色 SUV 以公里为单位,试图抓住它的脚后跟。我们正飞往图瓦地理的尽头——埃尔津地区,位于库热格峡谷,与蒙古接壤。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臣民没有时间更正主管当局的许可,但我们决定冒险一试。 Kuzhege 翻译自图瓦语,意为“辫子”。山脉看起来确实是柳条状的,非常类似于古代西部“麦肯纳黄金”行动展开的地方。当然,Kuzhege 低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但深谷本身,这些不寻常的花边墙出现的地方,似乎是为各种隐蔽的事务而设计的。两山之间有一夹缝,后面是几条蜿蜒的石廊。在走廊里,整个芭比城市都有塑料锁、汽车、娃娃,甚至还有笑话银行的 500 卢布纸币。有人向这里的神灵要孩子,有的要车子,有的要房子,有的要钱财。我们不过是祝福。然后仪式开始了,在他愤怒的呼吁中,肯突然举起手鼓定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双手垂下,将羽毛头饰摘下,连后脑勺都说出了深深的震撼。原来是一股火红色的流光从峡谷中倾泻到肯的身上。显然,灵体清楚地表明他被听到并注意到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 Tash-ool Buuyevich 的兄弟身边停留,他住在离峡谷不远的地方,是一名牧羊人。一进屋,就迎面撞见两个身穿军装的图瓦巨人。边防军!带着紧张的微笑,我们坐成一排,英国女王的臣民正试图与墙融为一体。
- 你身高多少? - 无耻地感兴趣。 – 你可能是图瓦最高的?你在当地的篮球队打球吗?不玩?你用双筒望远镜看到间谍吗?你是骑马来的吗?你有很多吗?有骆驼吗?
这话一出,边防官们都愕然摇头。
-我们在萨拉托夫地区有一位州长,他拥有一头私人骆驼、一整座动物园、一栋豪宅、一架飞机和一艘轮船,然后他不再担任州长,一切都被剥夺了-一个飞机,轮船,豪宅,动物园和骆驼! - 我正在向边境守卫扔一场坦率的暴风雪。
他们沉默了很久,然后一个人小声的“cha”了一声——好!
“恰恰,”另一个人笑道。现在隔阂被打破了,谢天谢地,紧急检查文件的想法消失了,很快边防人员自己开始了,他们坐在小马身上,双腿几乎垂在地上。可惜我们不允许拍照。在返回的路上,懂得如何在完全相同的俄里导航的 Tash-ool Buuevich 要求停车并带我们去土墩。这是一块像歪牙一样从地里伸出来的鹿石。甚至想想他用他的观点撕开多少个世纪都是可怕的。上面没有任何图画,巫师们用手掌抚过粗糙的侧面,形成了一个荣誉圆圈。我跟在后面,向车走去,脑子里清楚地听到一个建议,那就是掏出我的口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它的脚下。而已!我涂了口红、塑料口香糖和一些硬币。我很庆幸我把手机忘在车里了。
这就是来龙去脉。几个世纪前,在这些荒沙的某个地方,一位佛教僧侣发现了一个彩虹体,离这里不远就是 Tash-ool Buuevich 力量的发源地,他们还说在当地的山谷中,荒芜如火星景观,V.V. 之一。普京。
在错误记忆的存钱罐中,它完全处于底部。这是一张我们晚上看连续剧的照片。 Tash-ool Buuevich 叹了口气,低声说:“你的伙伴!”在急剧的情节曲折中,当爱情线停顿时担心,然后开始讨论那边那个戴着高冠的混蛋是真的还是我们的情报官。早上,这个将电影故事如此贴近自己内心的人,讲述了他如何与三个认为他可以被殴打和抢劫而不受惩罚的白痴打交道:
- 我说“你会死”并派出了一个恶魔。
结果,一个白痴很快就死了,另一个呆了七年,为了寻找第三个,两个月后,一个女人来找他,一个萨满。
- 我不知道那是他的母亲,我说尸体在森林里。然后我发现了她是谁,她在找谁。
他还讲述了他曾如何担任护林员,为了扑灭偷猎者专门放的火,他只是下雨。至于五年来他第一次给他的亲戚算命,并说他会在狩猎中找到谁。在社会主义发达的年代,警察偷偷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从照片上看到了什么。
- 区警察局长的一个亲戚失踪了,整个警察都在寻找,找不到。我说尸体在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不,他说,我们已经把整个房子翻了个底朝天。搜索,我说,搜索。原来是我指挥了这个老大。在墙上,我说,房子后面会有一把铲子,拿着它去挖。他们正在挖掘,疲倦,不相信,他们想放弃一切,但在一米半的深度发现了尸体。
我记得病人的流动(“我帮助人们一点点”),咒语的喃喃自语,密密麻麻,甚至挂着斧头,香火冒烟。以及对现代手鼓的尖酸刻薄的话:
- 一个房间里有十个萨满和治疗师接受!是啊,这怎么可能!那就是力量!以前,有两三个巫师在这片区域积极活动,但现在不可能了,神灵互相干扰。
当然,作者不明智地处理掉了这个机会。他可以乞求健康,可以乞求钱,可以乞求孩子上大学,但要么拿着相机到处跑,要么摸索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同样,中心图像仍然完全未显示。但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中心,小疯人院绕了五天的轴心,所以他,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被最后想到。此外,如果你不真正了解第一层天空,你会写什么关于第九层?
然而,他们设法从内非取出了他们的小违禁品,即没人能看到的精神武器。只是每当可怕的现实再次尝试昆虫、四肢着地、弯腰并证明你根本不配比平凡的任何东西时,你就会立即记起早晨的鸟儿以音符“盐”开头,那窗外的树像绿色的大心脏一样在跳动,你头顶的天空是巨大而自由的。此前,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科济列夫 (Nikolai Kozyrev) 就住在这片天空下,守卫们在谴责中写道:“在一场战斗中,他说存在并不总是决定意识。”现在白龙活着,就像七个世纪前的埃克哈特大师一样,上帝从不向他隐瞒任何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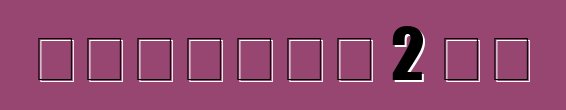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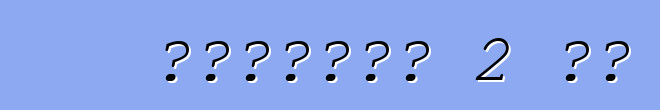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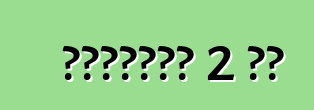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54:58 +0300 GMT
0.010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