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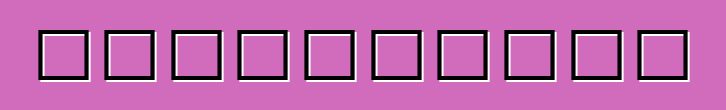



我們家族有數十代巫師起源。我父親從 Verkhneudinsk 的一所蘇聯黨校畢業後,領導了 Krasnaya Molka 公社,成為 Balagansky 區集體農莊工會的主席,在烏蘭烏德建立了一個 PVZ,並且是療養院的主任。然後,當“黨的政策的積極指導者”在伊林卡的一個狹窄的親戚圈子裡突然進入恍惚狀態並脫口而出薩滿祈禱時,所有人都震驚了。我們的客人,塔蘭塔耶夫兄妹,對這次突如其來的襲擊感到驚訝。與丈夫一起被捕並穿過古拉格集中營的蒙古共產國際前僱員維拉·馬克西莫夫娜說:“永遠不要再這樣做了!這樣的行為對於黨內老兵來說是不允許的。”吉洪馬克西莫維奇,前軍醫,也是無神論者,微笑著若有所思地說:“在這個儀式中有一種如此強大,如此迷人的東西,不幸的是,我們已經失去了。”
我的叔叔柏拉圖·巴爾圖科夫 (Platon Bartukov) 患有薩滿疾病,從小就開始接觸薩滿。但在 1920 年代,屈服於反宗教宣傳,他與我父親一起燒毀了我們著名祖先薩滿 Borte 的面具和其他保存在蒙古包最尊貴的地方的 ongons。一場大罪影響了他們的命運。柏拉圖瓦西里耶維奇變得跛腳,很難找到工作,他在監獄裡。我父親也很痛苦——他曾三次被開除黨籍,找工作也遇到了問題。
我們家的長子都是男孩。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父親以此為榮。也許是因為強大的薩滿家族的傳統以這種方式得以保留?畢竟,男人被認為是
返祖歸根
與我的祖先不同,我出生在一個無神論時代。因此,他沒有受洗,就像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樣,不存在巫師啟蒙的問題。少先隊員、共青團員、黨員。此外,從莫斯科國立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除了一門關於無神論的特殊課程外,一切都充滿了唯物主義,我在報刊上發表了反宗教宣傳的文章。
十年前,我開始編輯《佛教》雜誌。在莫斯科與達賴喇嘛會面,隨他的隨從前往卡爾梅克、圖瓦、布里亞特,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我看來,我在哲學係對他有所了解,我們在那裡研究所有宗教,包括佛教。但我看到了最古老宗教的真面目,當然,只有那時。
除了一切,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了薩滿教。事實是,佛教起源的古老西藏苯教教義本質上是薩滿教。很多古老的儀式,佛教的傳統,例如邪教
當我開始與巫師會面時,令我驚訝的是他們都立即在我身上感受到了我的薩滿教義。著名的烏干達婦女 Nadezhda Stepanova 第一次見到我,對我一無所知,她說她在我的光環中看到了很多行的薩滿教守護者,其中一位是最強大的 - 以一位老婦人的名義.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家有個巫師奧尼東,是俄羅斯人民藝術家舞蹈家T.E.的曾祖母。 Gergesova 和我的高曾祖母。顯然,斯捷潘諾娃在我的監護人中看到了她。
當我問娜傑日達·阿南尼耶夫娜她對這一切的感受時,她回答說:“我看到了一切。”當被問及 shamanic utkha 如何在今天表現出來時,她說:“表現形式可以不同。顯然,你寫作、作曲。其他人成為科學家、藝術家。”從進一步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這些類型的創造力都類似於薩滿教,它不會在後代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想到我的 zayan-keepers,我想起了一些似乎可以證明他們的案例。遇到危險時,我會聽到類似耳鳴的聲音,警告我可能有災難發生。這種“響鈴”可能發生在完全無害的情況下,乍一看,在街上,在電車裡,在隊列中,但後來發現警報的原因和“警報”的激活是相當真實。
預言之夢
我不知道預言夢算不算是薩滿能力的體現,但好幾次做夢簡直讓我驚嘆。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十二月黨人 N. Bestuzhev 的後代,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 找到了他們。在多篇文章中,我呼籲向這個十二月黨人的兒子 A. Startsev 致敬,他在 19 世紀末為濱海邊疆區和整個俄羅斯做出了很多貢獻。一天早上,我做了一個奇妙的夢。在一個月夜,我沿著斯塔爾采夫莊園所在的普佳京島漫步。我在他的墳墓旁看到一大片白雲。我從下往上看著他,不寒而栗:雲朵勾勒出十二月黨人之子的臉龐。他嚴厲地看著我,研究,然後他的表情柔和下來,他甚至微笑著對我點頭:
我醒了,對一個愉快的夢感到驚訝,因為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來尋找,這是成功的加冕,現在 - 斯塔爾采夫本人點頭感謝我。想像一下,幾天后,當我從他後代的一封信和報紙上得知,就在那天,在普佳京島上為斯塔爾采夫修建了一座紀念碑時,我感到很驚訝。當時是莫斯科的清晨,此時是濱海邊疆區,但早了七個小時(這是時區的差異),隨著人們、攝影記者、電視記者的匯合,我的舊夢成真了——記憶一個了不起的人永垂不朽。
遺傳從小就表現出來
薩滿教根源也體現在我的親戚身上。它們在我表兄弟 A. Garmazhapov 和 A. Norboev 的孩子身上尤為明顯。 VSGAKI的學生Lena Garmazhapova看到了十二歲以下人的氣場,稱之為顏色、形狀。我可以告訴誰最近吃了什麼,因為。顯著的內部器官。她還看到了“雙胞胎”、“監護人”。在祖父家,博裡看到附近有一位“喇嘛叔叔”。沒有人知道他有一個叔叔——一位喇嘛,當她說出這句話時,祖父博里亞證實他真的有這樣一個叔叔,他和其他喇嘛一起在 37 年被流放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她告訴 Baba Lyola Baraeva,她的妹妹圍著她跑。這位姊妹在 20 多歲時就去世了。她對阿姨加利亞說:“阿姨,舅舅就在你旁邊。”他們都去了 Sagaalgan 的 Ivolginsky datsan,舉行了祈禱儀式,之後莉娜說現在他們旁邊沒有人了。祈禱移除了影響難以預測的<衛星>。不僅可以保護他們,還可以趕往下一個世界。
當加利亞阿姨開始使用超感知覺,開始為人們療傷時,莉娜開始幫助她,因為我看到了黑色的能量,並且可以分辨出“黑色”仍然存在的地方。因此,她幫助治癒了 Baba Lyolya、祖父 Borya 和其他親屬的傷勢。關於她的一位熟人,她說她“從附近的每個人那裡汲取能量”。少女對能量吸血術一竅不通,但她說,為了保護自己,她不得不對自己說:“別喝酒,給我能量。”它有所幫助。
進入一間公寓,莉娜整個人都縮了縮,緊張起來。 “你怎麼了?”。 “他們就坐在那個房間的那邊。” “他們是誰?”。 “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們,但它們有很多,在天花板上,在枝形吊燈上,我很害怕它們。”後來證明,損壞是針對公寓的業主。儘管公寓面朝陽光,但角落都結冰了,屋子裡很冷。不久,其中一名居民死於車禍,其他人則患上了疾病。
Seryozha 和 Dima Norboevs 看到了光環。他們說,在健康人身上,它是皇冠的形式,一個粉紅色的光環,而在病人身上,光環是黑色的、撕裂的、“多刺的”。 Seryozha 矯正頭部,治療頭痛。
有些人將這些能力的消失與青春期、聲音突變和其他我們還不知道的孩子身體的變化聯繫在一起。據信,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有能力看到盤旋在我們周圍的人、靈魂、守護者和吸血鬼的光環。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種
如何找出你的薩滿教徒?
近年來,人們對薩滿教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沒有人禁止tailagans,其他集體祈禱和儀式。由於薩滿巫師一直代表著特定的氏族,所以首先要恢復自己的家譜,記住父母的所有祖先。在此期間,他們中是否有薩滿巫師將變得清晰。通常,從同胞的故事以及科學家的出版物中可以很容易地確定這一點。在 M. Khangalov、S. Baldaev、M. Manzhigeev、D. Dugarov、T. Mikhailov、L. Abaeva、N. Zhukovskaya 等科學家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們祖先的棲息地和遷徙地,找到從他們來自哪裡的調用中,他們後來去了哪裡。
由於現在布里亞特社區不僅根據其棲息地出現,而且還根據其屬出現,因此這項任務也變得更加容易。在烏蘭烏德,一個奧爾洪布里亞特人協會已經運作了將近十年,Alagui、Lono、Buure 等部落在其中進行必要的祈禱。
西藏喇嘛在特殊訓練的幫助下獲得視力,之後喇嘛打開所謂的第三隻眼。對於有薩滿教根源 (utkha) 的人來說,這些能力會在薩滿疾病和獲得薩滿或 udaganka 頭銜的特殊啟蒙後恢復。所以不必害怕薩滿病,雖然它帶來痛苦和難以忍受。你只需要及時求助於你的部落薩滿,他們會說這個人是否值得啟蒙,以及應該在何時、如何以及在何處進行啟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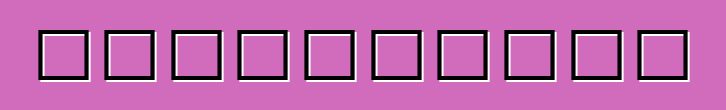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36:26 +0300 GMT
0.010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