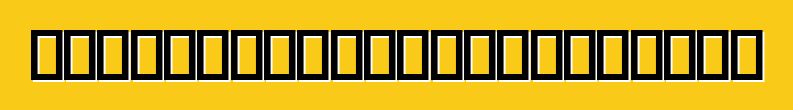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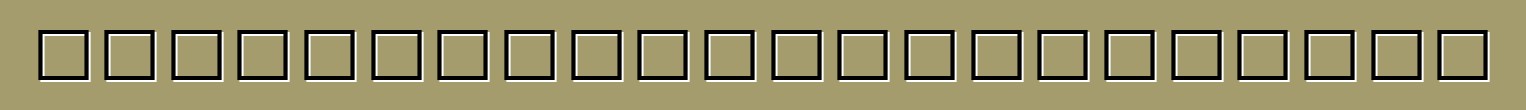




致幻劑和精神藥物是世界許多民族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無論我們轉向世界的哪個地區,我們都一定會遇到當地藥物的使用。墨西哥人民長期以來一直使用致幻的仙人掌 (mezcal) 和 psilobicine 蘑菇,在南美洲他們咀嚼古柯葉,在北部和中部他們吸入煙草煙霧,大洋洲人民釀造了一種令人陶醉的飲料——從胡椒根中提取的卡瓦酒植物,在亞洲,他們食用各種基於大麻和罌粟的藥物,在中非 - 從可樂樹皮中提取的飲料。此外,致幻劑的消費通常與儀式和儀式實踐有關,並且具有非常古老的歷史傳統,已為眾多書面資料和考古發現所證實。
必須假設在公元前很久以前就在西伯利亞。 e.當地精神藥物的醉人特性是眾所周知的——大麻、天仙子、野迷迭香、豬草和其他自古以來就在歐亞大陸用於製備麻醉藥品的植物。一個已經成為教科書的例子 - “Scythian bath” - 希羅多德描述的黑海斯基泰人集體吸入大麻煙霧的方法,恰好在西伯利亞找到了考古證據。在 5 世紀挖掘 Pazyryk 土墩期間,在 Gorny Altai 的領土上。公元前。在永久凍土的鏡頭中發現了保存完好的斯基泰麻醉劑時期的配件 - 小圓錐形小屋覆蓋著毛氈和皮革,其中一個下面有青銅器皿,上面有燒焦的石頭和燒焦的大麻種子,一個裝有大麻種子的皮袋綁在上面另一個的極點 (Rudenko, 1962)., pp. 242–243)。
大多數情況下,西伯利亞人民的麻醉經歷與另一種植物 - 木耳有關。目前,關於在西伯利亞人民的儀式和儀式實踐中最廣泛使用木耳的奇特科學神話已經形成。它在西方歷史學家和民族藥理學家中尤為常見(Wasson,1968 年;McKenna,1995 年;Jasm 和 Thorp,1997 年)。此外,食用飛木耳必然與西伯利亞薩滿教有關,在世界古代和現代人民的採蘑菇儀式中發現了許多與薩滿迷幻藥的相似之處。但這真的是這樣嗎,致幻蘑菇在西伯利亞如此普遍嗎?西伯利亞薩滿教與飛木耳的精神藥性之間的聯繫有多緊密;西伯利亞巫師一般是如何使用藥物的?本文試圖理解這些問題。
鵝膏菌和鯰魚:科學神話的誕生。
民族真菌學 [1] 的創始人 Gordon 和 Valentina Wasson 首次注意到麻醉蘑菇(包括飛木耳)在儀式實踐中的作用。他們發現了美洲和古代歐亞大陸存在蘑菇崇拜的許多例子,這使他們甚至可以將世界上所有的人分為真菌愛好者和真菌恐懼者。在他們的共同工作中,這對夫婦提出了另一個原始假設,根據該假設,著名的吠陀經 soma 是在帶有紅色帽子和白色斑點的蘑菇的基礎上製備的,即來自飛木耳 (Avanita muscaria) [Wosson,沃森,1957]。最後一個想法由 G. Wasson 在他的書“Soma:不朽的神聖蘑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他甚至指出了製作這種飲料的傳統的可能起源時間和地點 - III 之交的西伯利亞 -公元前二千年,將它在印度的出現與雅利安人的重新安置聯繫起來 [Wosson, 1968]。 R. G. Wasson 的假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神話學的主要研究人員對此做出了回應 [Levi-Strauss, 1970; Elizarenkova 和 Toporov,1970]。在批評某些有爭議的條款的同時,整個假設被接受,毫無疑問,飛木耳在西伯利亞人民的薩滿教實踐中被極其積極地使用。 T. Ya. Elizarenkova 和 V. N. Toporov 甚至發展了這個想法,將關於飛木耳的想法與薩滿(世界)樹的語義聯繫起來,並找到確認飛木耳和鯰魚之間聯繫的變體,G. Wasson 沒有註意到 [Elizarenkova , 托波羅夫, 1970]。
民族真菌學的形成和圍繞它展開的討論,除了毫無疑問的富有成果的結果——引起人們對真菌在神話中的作用的關注之外,還產生了幾個相互關聯的結果,主要是對西伯利亞的研究。首先,有一個堅定的想法,即把木耳當成薩滿蘑菇;其次,開始尋找確認西伯利亞古代人口文化中蘑菇儀式的存在;第三,西伯利亞人民對所有麻醉劑和致幻劑的消費開始完全與薩滿教聯繫在一起。回想一下,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蘇聯不言而喻地禁止藥物研究的背景下發生的。
在西伯利亞尋找考古證據。
古代存在蘑菇儀式的想法幾乎同時出現在西伯利亞的考古學家 - 原始藝術研究人員中。 1971 年,N. N. Dikov 在楚科奇出版了 Pegtymel 的石刻,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 - 公元一千年,其中一些包含“蘑菇”情節:戴著蘑菇帽和蘑菇狀物體的擬人化人物。作者將它們解釋為人飛木耳和飛木耳,發現古代特定蘑菇儀式的存在得到證實,主要是與亞洲最東北部人民的麻醉會議的民族志相似 [Dikov, 1971; 1979] (158–159)。
繼 N. N. Dikov 之後,M. A. Devlet 以同樣的方式解釋了葉尼塞薩彥峽谷岩畫中戴著寬“蘑菇形”帽子的擬人化圖像,將它們與西伯利亞的毒蘑菇崇拜聯繫起來。這些圖像的年代也非常廣泛 - II - I 公元前一千年。 (達夫萊特,1975 年,1976 年)。儘管沒有任何嚴肅的論據,該假說還是找到了權威的支持者。 A. A. Formozov 提議將這些圖像與在亞洲廣為人知的令人陶醉的蘇摩飲料的生產聯繫起來(Formozov,1973 年,第 264 - 265 頁)。在這個地方,考古學和神話學的研究路線終於結束了。 G.M. 在書中以最詳細的方式介紹了兩者。 Bongard-Levin 和 E. A. Grantovsky “從斯基泰到印度”。參考 R. G. Wasson 的觀點,作者還認為木耳可能是古代印度-伊朗人可以從中製備軀體的植物之一,甚至在印度-伊朗人民的宗教傳統中建立了一個關於存在的優雅概念“一系列北方薩滿教的基本特徵”(Bongard -Levin, Grantovsky, 1983, pp. 119–121)。特別有趣的是,這個由神話研究人員提出的想法從考古學家那裡得到了反饋。因此,E. M. Meletinsky 引用了一個關於 Itelmens 中的飛木耳女孩的神話故事,正在 Pegtymel 的岩畫中尋找證實(Meletinsky,1988)。
上述研究人員的權威性如此之高,假設的規模和表現力如此之大,而且通過民族誌類比證實了作者最廣泛的博學,以至於下一代考古學家似乎已經拋棄了所有的疑問。在遠東考古學中,傾向於將所有類似於蘑菇的物體解釋為木耳,並將它們與致幻植物的崇拜聯繫起來,參考公認的權威並引用非洲、亞洲和非洲人民對它們的使用最廣泛的類比。美國。這就是 M.A. Kiryak 在楚科奇西部考古遺址的石頭上看到蘑菇圖像的方式(Kiryak,1998 年,第 106-109 頁,圖 1、2); A. G. Garkovik 在來自濱海邊疆區 Evstafiy-4 定居點的粘土物體中 (Garkovik, 1988, pp. 50–54, fig. 1)。這些作品無可爭辯的優勢是年代相當準確:在第一種情況下,放射性碳測年為公元前 2500 年,在第二種情況下,根據文化層的年代測定,下半葉是公元前 3 千年末。最後的日期是最早的,但作為飛木耳雕像的帽子碎片呈現的粘土物體與原型只有遙遠的相似之處。順便說一句,這同樣適用於其餘圖像。古代藝術研究人員對蘑菇研究的精髓已成為 M. A. Kiryak (Dikova) 書中的一個章節(Kiryak,2000)。在這裡,與其他此類作品一樣,大量參考了前人,甚至在作者不知道的作品中也經常發現真菌(Okladnikov,1976 年;Okladnikov 和 Zaporizhskaya,1969 年,1972 年;Tivanenko,1990 年);來自V. N. Toporov (Toporov, 1987) 的作品,在他們的解釋中不僅不證實考古地塊,而且經常與他們相矛盾,R. G. Wasson 的強制性腳註,其質量毫無疑問是從 M. A. Devlet 複製的(相同標題中的錯誤實際上表明作者沒有看過這本書),最重要的是,作者完全缺乏關於早期信仰形式的想法,儘管如此,這些信仰卻經常被提及。
在考古學家解釋蘑菇形物體的嘗試中,新西伯利亞研究員 A.P. Borodovsky 的假設脫穎而出,他找到了一種更合理的方法來解釋在鐵器時代早期的 Bolsherechenskaya 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五件粘土物品的用途.他認為它們是陶瓷生產中用來平滑容器壁的砧座。與他的同事不同,A.P. Borodovsky 沒有引用推測性的觀點和遙遠的類比來證實這一點,而是引用了實驗數據,其結果是非常有形的。儘管正是這些材料的“蘑菇狀”性質是最沒有疑問的,因為它們確實是蘑菇狀的物體:它們有一個凸起或扁平的帽子,在一個帶孔的短莖上有懸垂的邊緣,在帽子內部有小孔(完全不起作用)。總的來說,正是上述所有項目中的這些項目與飛木耳最相似。順便說一句,他們發現的情況也最不適合他們的功能解釋。五分之四的鐵砧是在墓葬中發現的,所有這些都在男性墓葬中(Troitskaya, Borodovsky, 1994, pp. 119, 121, 126),儘管在養牛業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社區中的陶器很可能是,應該由女性完成。此外,還發現了一個鐵砧以及一個石製香爐、幾塊粉筆和一面銅鏡——一種魔法儀式複合體(Troitskaya,Borodovsky,1994 年,第 121 頁)。應該指出的是,關於後一種情況,古蹟發掘的作者 T. N. Troitskaya 以前認為 Bolsherechensk 人的蘑菇形物體是儀式。考慮到 A.P. Borodovsky 的假設,我們不得不說,即使對於考古學家來說,蘑菇形人物是否是木耳菌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大爭議。
國內岩畫師的作品整體上從時間和空間上為亞洲蘑菇崇拜的傳播描繪了一幅相當完整的圖畫。如果他們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在公元前 3 千年末,亞洲東北部就開始使用木耳。而且,這一傳統直到民族志現代性才被打斷。考慮到薩彥峽谷的發現,與我們這個時代相比,古代致幻木耳的分佈區域正在顯著擴大,它包括南西伯利亞,並與中亞蘑菇崇拜融合,從中獲得了著名的鯰魚。在這種情況下,北方人關於木耳的想法可能是從中亞和南亞人那裡衍生出來的,並從外部出現在針葉林地區,這種可能性是相等的;反之亦然,他們從北方來到這些地區。這裡確實存在重大反對意見。首先,空間在古代是文化交流的嚴重障礙,此外,在民族誌時代,除了亞洲針葉林地區外,任何地方都不知道食用木耳,具有致幻特性的木耳只在某些地區生長,這是現代民族藥理學家和遠見者的實驗證實了這一點。其次,即使你在石像中看到蘑菇,也不一定是木耳。總的來說,所有作品中蘑菇形形象與木耳的聯繫,都是通過北方民族誌類比進行的,又必然與薩滿教聯繫在一起。 “在關於西伯利亞和遠東人民的民族志的文獻中,有大量關於薩滿巫師使用飛木耳(或從中提取的飲料)[2] 來達到狂喜狀態的信息,其中“第二個願景”打開(Kiryak,2000),-這是考古學家關於問題本質的典型想法。最有趣但也最脆弱的是飛木耳形象的“薩滿”基礎。為了澄清這種情況,讓我們看看在西伯利亞人民的傳統文化中,木耳究竟是什麼。
西伯利亞北部人民對鵝膏菌的消費。
食用毒蠅傘 (Amanita muscaria) 的傳統在西伯利亞東北部的人民中廣為人知。 VG Bogoraz 認為,飛木耳令人昏迷和興奮的特性是由“東北亞原住民”發現的(Bogoraz,1991 年,第 139 頁)。 1787 年,東北地理探險隊的一名成員在 Itelmens 中觀察到它:“......不喜歡木耳,也許,因為缺乏木耳,他們試圖喝那些發瘋的人的尿液,因此他們比第一個更瘋狂“(白天記憶......第170頁)。眾所周知,食用蠅傘在科里亞克人中尤為普遍;南太平洋的楚科奇人和南部的 Itelmens 群體也使用木耳。然而,在這裡,在人種學時代,這些蘑菇的消費也受到以下事實的限制,即並非所有類型的飛木耳都具有精神特性,而且,它們僅生長在針葉林地區,並且可以開采的數量極其有限。但幾乎所有西伯利亞東北部的居民都知道這些蘑菇的醉人能力。甚至那些自己不使用木耳的團體也收集它出售給他們的鄰居——苔原馴鹿牧民。楚科奇人最常使用乾燥形式的木耳。蘑菇是為將來收穫的,曬乾後每根線串三片。使用時,撕下小塊,充分咀嚼,用水吞服。這是科里亞克人的一個普遍習俗,一個女人嚼一個蘑菇,然後把它交給一個男人,讓他吞下口香糖 (Bogoraz, 1991, pp. 139–140)。注意在西伯利亞東北部關於發酵,即他們不知道用蘑菇製造飲料,因此與特製索瑪的直接聯繫非常值得懷疑。
顯然,在俄羅斯人到來之前,飛木耳的麻醉特性不僅為西伯利亞東北部的人民所熟知。有證據表明,它們曾被雅庫特人、尤卡吉爾人和鄂畢烏格里人使用。此外,在西西伯利亞,木耳生吃或喝乾蘑菇湯。 I. G. Georgi 對這種藥物在漢特人中的消費和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描述:人一時食一新鮮木耳,或一飲酒,三取一飲,曬乾,受此之後,先是多談,後自下而上,切得歌唱、跳躍、驚呼。 ,創作愛情,狩獵和英雄歌曲,表現出非凡的力量等等,但之後他什麼都不記得了。在這種狀態下度過 12 到 16 個小時,最後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用力很大,像個釘了釘子的人,但喝醉了,腦子裡就沒有那麼重的負擔了,喝醉之後,也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Georgi,第一部分,第 72 頁)。上面的引文相當準確地描述了攝入生物鹼——最常見的植物藥物——引起的麻醉狀態。
紅木耳的成分包括兩種生物鹼 - 毒蕈鹼和肌托品。第一個是最強大的。屬於極強毒藥。一個人同時攝入 0.005 克會導致最嚴重的後果,甚至死亡。與其他生物鹼一樣,它只能用作小劑量無毒的興奮劑。然而,毒蕈鹼不會引起致幻作用,假設促肌素(蘑菇阿托品或毒蕈鹼)作用於大腦(Astakhova,1977),儘管尚未對人體進行促肌素試驗,這只是一個假設。不管怎樣,食用含有毒蕈鹼的木耳是極其危險的,需要非常準確地計算劑量。
從上面給出的例子來看,西伯利亞人民非常了解“平均”劑量 - 三個蘑菇。但劑量的大小通常取決於身體的一般身體狀況、食用持續時間、劑量之間的間隔。年輕人少量使用蘑菇,劑量逐漸增加,劑量間隔縮短,有可能在麻醉夢後以最小劑量立即重複中毒。 V. G. Bogoraz 詳細描述了楚科奇人中毒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可以單獨發生,也可以在一次服藥期間依次發生。在第一階段(年輕人的特徵),愉快的興奮開始,無緣無故的喧鬧歡樂,靈巧和體力得到發展。第二階段(多見於老年人)出現幻覺反應,人們聽到聲音,看到精神,整個周圍的現實對他們來說呈現出不同的維度,物體看起來過大,但他們仍然意識到自己並正常回應熟悉的日常現象,他們可以有意義地回答問題。第三階段最難——人進入意識改變狀態,與周圍的現實完全脫節,處在虛幻的神靈世界中,受神靈控制,但能長期活動,能動能說話, 之後一個沉重的麻醉夢開始了 (Bogoraz, 1991, pp. 140–141)。
但以上所有證詞都與薩滿教習俗無關;這裡我們更多地談論家庭毒癮。像所有麻醉藥物一樣,飛木耳引起典型的中毒;從攝入開始,身體對生物鹼產生依賴。飛木耳的習性很強,在沒有蘑菇的情況下,情侶們喝自己的尿,或者最近吃過的人的尿,有時甚至是在蘑菇區吃草的鹿的尿。毒蕈鹼和 mycoatropine 在體內幾乎不被分解,而是以溶解的形式從體內排出,因此尿液幾乎與蘑菇本身一樣有毒。西伯利亞人民也很清楚這一點。顯然,他們關於木耳的特性的知識是食品實驗的結果,是根據實際使用經驗發展起來的。無論如何,早在 18 世紀,北方人民就已經了解劑量和消費規則。穩定。這本身就表明蘑菇的消費必須經過一定的測試階段,在此期間制定了食譜和標準。考慮到致幻的木耳菌並非隨處生長,而且它們的精神活性會隨著每年的氣候變化而變化,不得不說這個階段一定是相當漫長的。即使是堪察加半島的俄羅斯人,他們從當地人那裡借鑒了現成的消費傳統,也已經度過了這個階段。 S. P. Krasheninnikov 給出了幾個俄羅斯人在這個階段食用木耳的可悲例子“僕人瓦西里·帕什科夫,經常奉命訪問上堪察加和博爾謝列茨基,命令木耳將他的卵壓碎,誰在三天內聽了他的話,死了。對於和我一起來的翻譯 Mikhail Lepekhin,他不知道喝木耳,他命令切開他的肚子……”(Krasheninnikov,1949 年,第 694-695 頁)。
自然地,飛木耳會影響心靈,在某些情況下會引起致幻反應,從而提供與精神世界的聯繫。將消費者帶入神聖的境界,木耳自身獲得了神奇的力量。在這裡,顯然應該在消費動機中尋找神聖與世俗之間的界限。從給出的描述來看,這些蘑菇的大量使用絕不是為了神奇的運動,而是一個純粹平淡無奇的目標。如您所知,吸毒會導致興奮,刺激中樞神經系統,導致欣快狀態。皮質抑制的結果是大腦皮層的活動受到抑制,思維活躍、記憶力、情境情緒受到抑制,但同時積極情緒(喜悅)中樞的興奮性增加。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癮君子有吸引力的是後者。因此,我們必須指出,西伯利亞北部人民對木耳的大量消費存在於儀式和禮儀實踐之外,最多與它平行。
神話和儀式中的鵝膏菌。
木耳作為傳統飲食文化的一種現象,自然而然地在食用它的人們的神話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古代意識的麻醉幻覺與任何其他現像一樣真實,並且無疑需要命名和解釋。因此,在楚科奇人中,蘑菇被擬人化為一種精神 - 一種飛木耳,它像真正的蘑菇一樣呈現 - 沒有脖子,沒有腿,有圓柱形的身體和大頭,儘管它可以出現多種多樣形式。他移動,快速旋轉。根據楚科奇人的說法,飛木耳的靈魂非常強大,它們會穿過石頭和樹木生長,撕裂和粉碎它們。他們與下界有聯繫,無論如何,他們經常帶領他們的仰慕者到死者居住的國家[T。 Ya. Elizarenkovka 和 V. N. Toporov 認為,通過飛木耳的恍惚狀態可以與上層世界聯繫],在這方面,他們非常危險和陰險,他們需要一個人不斷尊重自己和周圍的自然,他們迫使他們執行他們所有的命令,不服從就以死相威脅,他們經常開惡作劇,以虛假的形式展示一些東西。 (Bogoraz,1991 年,第 140-141 頁;他,1939 年,第 5 頁)。 Ob Ugrians 還認為飛木耳中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根據 M.V. Shatilov 的說法:“雙關語”(飛木耳 - A.Sh.)......當一個人知道從他那裡偷東西,誰欺騙他等的一切時,就會告訴他一個特殊的狀態。”
使用飛木耳,人們很容易接觸到它們,獲得它們的一些神秘力量,有時它們甚至可以自己變成(感覺)蘑菇。顯然,只有某些人,最有可能是生理上易感的人,服用木耳的持續動機之一恰恰是渴望與精神世界接觸,獲得自然元素精神賦予的新神秘機會。這種現像在西西伯利亞很普遍。在漢特人中,飛木耳被英雄故事的表演者食用。 “......這位歌手為了獲得更大的靈感,在唱歌前吃了幾個飛木耳 - 7-14-21,即七的倍數 [3]:他只是因為它們而變得瘋狂,看起來像個惡魔。然後整晚他都用狂野的聲音唱著史詩,甚至很久以前,似乎都被遺忘了,早上他精疲力盡地倒在長凳上”(帕特卡諾夫,1891 年,第 5 頁)。正是這種個人經歷構成了有關飛木耳薩滿教本質的思想的基礎。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在西伯利亞薩滿巫師中,有不少“空想家”在吃完蘑菇後服用木耳或在麻醉夢中拜訪靈魂,從而進入恍惚狀態。在滿西族民間傳說中,薩滿被稱為“食蠅”人。曼西人的英雄故事之一講述了:“Ekva-Pyryshch 去了,帶來了薩滿。他在火上掛了一個裝有木耳的大鍋。巫師開始算命,有木耳,他打手鼓,他算命。 Ekva-Pyryshcha 即將發現這些技巧”(Chernetsov,1935 年,第 77 頁)。 K. F. Karjalainen 引用了 Khanty 中的幾個此類案例,男女巫師最常使用木耳來拜訪至尊天神 Sanka (Karjalainen, p. 306–307)。在漢特人中,在那些知道如何與精神世界接觸的人中,有一個單獨的木耳菌類別,“吃木耳菌並在半昏迷狀態下與精神交流的人”(Kulemzin, Lukina, 1992 , 第 120 頁)。一些涅涅茨薩滿巫師也服用木耳,以便從麻醉恍惚中的靈魂中找出如何治愈病人(Lehtisalo,p.164)。正是基於這些以及來自西西伯利亞的類似例子,薩滿教與食用飛木耳之間聯繫的假設才得以建立。但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木耳使用模式:在東北 - 褻瀆,幾乎所有社區成員都可以嘗試木耳;在西西伯利亞 - 神聖的地方,飛木耳僅供個人食用並嚴格按照儀式食用。但即使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也不完全是薩滿教的做法。人們認為,通過使用藥物來達到薩滿狂喜的陶醉並不是薩滿教的特徵。 Mircea Eliade 稱這種方法為“粗糙和被動的”(Eliade,p.175)。麻醉恍惚是相當前薩滿的,或神奇的。
在西西伯利亞西部,飛木耳的特性更常用於與精神接觸,但用於真正的醫療實踐。 V. N. Kulemzin (Kulemzin, Lukina, 1992, p. 118 - 120) 充分詳細地描述了 Khanty isylta-ku(魔術師和治療師)使用飛木耳的治療過程。整個過程歸結為讓病人入睡,長時間的睡眠和醒來。為了讓病人沉浸在睡眠中,isylta-ku 準備了一種相當複雜的藥物。他用溫水在兩個容器中浸泡木耳的干膜和沒有膜的蘑菇本身,而水必須是雪的,杯子是木製的,因為在任何儀式實踐中,違反既定秩序在這裡是不可接受的。服藥後,患者應在冷室中睡三天。治療師自己也帶了木耳,他必須和客戶一起去地下神 Kali-Torum 交出禮物,並請他不要帶走病人。在後者中,由於服用藥物,血壓下降,呼吸減慢,即發生非常嚴重的中毒,如果不小心或過量服用藥物,可能會發生呼吸中樞麻痺和呼吸停止。 isylta-ku的劑量,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因為他必須保持清醒,觀察熟睡中的人的狀態,及時將他從這種狀態中喚醒。 Khanty isylta-ku 的醫療實踐在語義上與 Carlos Castaneda (Castaneda, 1995) 描述的墨西哥魔術師唐璜使用麻醉仙人掌的行為極為相似。這裡排除了直接聯繫;相反,我們可以討論古代文化中麻醉藥品認知的普遍解釋模型。麻醉劑和致幻劑的類似概念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最多樣化的人群中廣泛傳播。但他們沒有真正的薩滿教基礎;從本質上講,飛木耳只不過是一種魔法元素。
另一方面,薩滿教屬於關於神聖世界的思想更發達的階段。在他的邪教實踐中,始終是人間與靈界之間的中介形象,他是被神選中的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不再只是一個人。但即使對他來說,精神世界也只有在儀式上才能進入,那時他會進入一種特殊的意識改變狀態——一種受控的恍惚狀態。同時,真正的薩滿入神術是不用藥物,而是藉助於歌唱、音樂、肢體動作、生物體質和長期訓練來達到的。還應該指出的是,在大多數薩滿儀式中,只有薩滿本人進入恍惚狀態;通常在場的人即使不是被動的觀眾,也至少不會安排舞蹈表演,就像人們在分析岩畫時所想像的那樣。在這方面,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所有民族都沒有發展薩滿教。在東北民族中,國內盛行薩滿教,當時幾乎人人都會薩滿教,在鄂畢烏戈爾人中正處於形成階段,吸收了夢師、魔術師、占卜師、占卜師和說書人的各種法術。並非沒有,在這些文化中,精神世界是非常有形的,即使不是每個人,許多人也有可能與之接觸。所描述的 18 至 19 世紀的民族正處於改變兩種催眠系統(魔法和薩滿)的階段。
恍惚的魔法技術,其中麻醉劑是一種變體,似乎先於薩滿教方法。神奇的是世界上所有民族與吸毒有關的儀式。薩滿教通過音樂、歌唱和肢體動作進入意識改變狀態的方法,是薩滿教發展形式的特徵,出現得晚得多,並逐漸取代了儀式中的麻醉恍惚。顯然,與此相伴的是,與靈界的集體接觸讓位於調解人的個人接觸,調解人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自然地,在這種情況下,吸毒可以作為遺物保留在薩滿教儀式中。
薩滿教實踐中的致幻劑。
在西伯利亞的針葉林地區,木耳似乎是唯一廣為人知的藥物,這可能是由於植物資源有限。在植物群更加多樣化和豐富的地區,含有精神藥物和致幻物質的植物範圍更廣,草藥的使用頻率更高。遠東人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麻醉品。在民間醫藥中,作為麻醉劑,有人參根、甜豬草、野迷迭香葉、杜松枝等成分。與飛木耳相比,這些是相當弱的藥物,不會引起嚴重的中毒或致幻反應。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的使用需要仔細的,通常是藥理學複雜的準備或幾種成分的組合。遠東人民使用麻醉藥品的方式更為多樣:麻醉植物被喝醉、咀嚼、焚燒和吸食。
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的使用也與薩滿教習俗有關。因此,Nivkh 薩滿必須在儀式之前和期間練習燃燒迷迭香(ledum palustrel、ledum hypoleucum)。一個特殊的吸煙者是薩滿的不變屬性,還有一條腰帶、一套西裝和一個手鼓 (Otina, 1994, p. 102)。 Udege、Ulchi、Nanai 和 Orochi 的巫師也在儀式中使用野生迷迭香。他們將事先準備好的干樹葉扔進壁爐或熱煎鍋中(Brekhman,Sem,1970,第 18 頁:Podmaskin,1998,第 57 頁)。煙霧影響了薩滿本人的心理,在封閉的房間裡創造了一個與靈魂交流的有利環境,促成了在場人員的集體催眠和薩滿恍惚。
在阿伊努人中,雲杉、落葉松、野蒜和當地名稱為 nutya 的植物的枝條在儀式前被放入熱灰中。後者是一種弱草藥。陰燃著,這些植物散發著芬芳的氣味,那煙霧顯然是一種微弱的鎮靜劑。在儀式之前,薩滿喝了鹹海水,海水中浸泡了雲杉和繁縷的枝條。植物的麻醉汁幫助薩滿達到了意識改變的狀態。在會議期間,薩滿又喝了這種液體兩三次,不斷保持身體的麻醉陶醉 (Spevakovsky, 1988, p. 168)。
顯然,在儀式的背景下包含精神藥物和致幻藥物是遠東人民消費文化的主要特徵。與精神世界的麻醉恍惚和致幻接觸似乎是這些植物營養用途的基礎。但是在遠東也沒有發達的薩滿教,而是記錄了它的早期形式。
在進入恍惚狀態的魔法和薩滿的連續變化中,我們可以追踪到一個趨勢:藥物越強,薩滿恍惚本身所起的作用越小;藥物越弱,受控催眠技術就越重要。在極端情況下,後者俱有像徵意義,幾乎不使用直接效果。如果我們考慮在醫療和儀式實踐中使用含有極少量麻醉物質的植物,這一點就會變得非常明顯。
一種這樣的植物是杜松 (Juniperus L.)。它曾經被西伯利亞的許多人使用,現在仍在使用,而且非常單調。杜松菸被熏蒸。燃燒的植物散發出令人愉悅的香氣,對人有放鬆和鎮靜的作用,西伯利亞的許多人認為這種香氣可以淨化心靈,對邪靈有害。因此,例如,在治療患有精神病的 Nivkhs 時,他們會用杜松樹枝上的煙霧熏蒸 (Otina, 1994, p. 98)。同時,煙霧的作用被解釋為不是麻醉(魔法),而是神聖(象徵)。擁有植物的並不是神靈,而是植物,通過煙霧,以自身的自然力量影響神靈,將他們驅離病人。
用杜松菸熏熏在西伯利亞南部尤為常見。在圖瓦,杜松 (artysh) 是儀式和儀式實踐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任何治療都從熏蒸儀式開始——驅除邪靈。一般來說,凡是可能有惡勢力的地方,都要進行熏蒸。這在葬禮和追悼儀式中尤為突出。所以,葬禮結束後,蒙古包必然要熏蒸,在與死者靈魂的親屬追思會上,巫師總是用杜松(san)點燃香爐(Dyakonova, 1975, p. 49, 60)。在專門分析圖瓦薩滿教必需品的著作中,通常會非常注意服裝、手鼓、鏡子和精神形象,通常對 artysh 沒有任何意義。 (Kenin-Lopsan, 1987, pp. 43–77)。然而,帶有乾杜松樹枝粉末或乾樹枝本身的燈是圖瓦巫師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我不止一次看到杜鬆在圖瓦薩滿巫師的實踐中的使用。薩滿會議通常從用 artysh 熏蒸開始。薩滿祭司點亮一盞燈或點燃一根樹枝,首先淨化他自己和他的工具。他通常按照一定的順序在陽光下將燈圍繞物體轉 3 到 9 圈:首先是木槌,然後是頭飾,立即戴在他的頭上,然後是手鼓,最後,他清洗自己將雙腳放在悶燒的 artysh 上 - 用左腳三次,然後用右腳,再用左腳兩次。在儀式之前,還通過在太陽下在臉上畫圈並將雙手交叉放在面前來清潔客戶。如果舉行大型儀式,所有在場的人都會以類似的方式用聖煙淨化。同時,在儀式期間,杜松必須不斷悶燒,以免熄滅,無論是薩滿本人還是從現有手錶中選擇的助手。高級圖瓦薩滿 Sailyk-ool Kanchiyr-ool 告訴我一個奇怪的細節。 Artysh 只能在室內持續燃燒,沒有必要在戶外燃燒。顯然,早期的杜松菸更多地用於與精神世界接觸。我不得不多次進入熏制杜鬆的房間,體驗它的醉人效果。在這樣的房間里呆久了,薩滿儀式通常會持續幾個小時,這種煙霧的麻醉效果會非常強烈。現在薩滿巫師使用杜鬆而不考慮它的麻醉特性,對他們來說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性的自然力量,而不是具體圖像中的人格化。在圖瓦薩滿巫師看來,artysh 有助於與精神接觸,以及諸如心、光、聲、純度等抽象的非個性化概念。
西伯利亞南部的其他民族對弱麻醉藥的看法也有類似的基礎。哈卡斯人還在任何治療前進行熏蒸儀式,並認為杜松 (Archyn) 的煙霧具有淨化作用。儘管用 Bogorodsk 草 (irben) (Thymus vulgaris) 進行熏蒸在其中更為普遍,但其麻醉效果與所描述的相似。給病人熏蒸時,治療師會說:“用須彌山的Bogorodsk草藥熏洗,/使人的邪惡力量得到淨化!/讓魔鬼回到他們的世界!” (Butanaev, 1998, p. 240)。
圖瓦和哈卡斯的巫師使用弱準備並不意味著他們根本不了解強大的準備。相反,是西伯利亞南部的人民知道合成的,因此非常強大的精神藥物和致幻藥物。合成藥物極其危險。除了強烈的刺激作用,藥物成癮的快速發作外,它們還最容易引起戒斷綜合症,即拒絕服用伴隨著精神功能的侵犯。即使是相對較短的休息也會導致行為改變、興奮性增加、易怒和攻擊性。那是典型的毒癮。我們主要談論通過昇華牛奶或穀物發酵產物獲得的烈性酒精飲料。圖維尼亞人和阿爾泰人長期以來一直在準備牛奶伏特加 - araka。哈卡斯人知道兩種烈性酒——“airan aragazi”——牛奶伏特加和“as aragazi”——黑麥伏特加 (Butanaev, 1998, pp. 143–149)。顯然,在西伯利亞南部開始生產這些飲料有著相當悠久的傳統,並且與經濟生產形式的形成有關。 V. Ya. Butanaev 認為,在吉爾吉斯汗國時期,哈卡斯的祖先就知道以穀物為基礎的令人陶醉的飲料,它們在中國的書面資料中有所提及 (Butanaev, 1998, p. 149)。
牛奶伏特加是南西伯利亞所有養牛民族都熟知的飲品,也有著相當悠久的消費歷史。早在中世紀,石雕腰帶上就描繪了一個皮革燒瓶,類似於阿爾泰人、哈卡斯人和圖瓦人的荒木燒瓶。 araki 的製造技術、存儲傳統和使用在突厥-蒙古世界的所有群體中都非常相似,並且在專業文獻中有相當全面的描述。
牛奶伏特加被解釋為一種象徵價值。它的使用不是魔法行為,它不提供與精神世界的直接聯繫。然而,它的語義負載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世界上養牛者所重視的乳製品的所有特性。 araki 的使用與一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時刻有關,他們在孩子出生、婚禮、葬禮、會見客人等時飲用它。事實上,這種合成藥物的消費伴隨著任何慶祝狀態,當日常生活退居幕後,社會框架擴大到普遍規模,使人們更接近自然精神的原始世界。阿拉卡和人類一樣受到精靈的喜愛,但它不是他們世界的價值,不像魔法階段使用的強烈植物迷幻劑,它不認同精靈本身。靈魂接受她作為祭品,被她吃掉並被她淨化,就像人一樣,他們與她一起度過一個假期,對人們懷有感激之情並象徵性地接近他們。在這種超越日常生活框架的相互狀態中,兩個世界——人類和神聖——之間被遺忘已久的神奇接觸方式得以體現。這些恰恰是藥物古老神奇功能的後遺症,它確保了它們在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的文化傳統中長期存在。
因此,致幻劑和精神藥物在西伯利亞人民的邪教實踐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很可能對應於它們使用的某些歷史階段,可以重建如下:
第 1 階段 - 測試 - 指的是人類探索西伯利亞的最早階段,當時許多植物只是在食物實驗中被品嚐過。
第 2 階段 - 魔法使用 - 意識到藥物的致幻作用,人們開始在魔法中使用它們,很可能是集體儀式。從未跨過這一階段界限的“蘑菇”考古器物和西伯利亞東北部人民對飛木耳的使用可能屬於這一時代。
階段 3 - 遺物使用,當精神藥物的力量僅由某些人在儀式和禮儀過程中使用時,最常見的是醫療實踐。正是在這個階段,遠東的人民,鄂溫克人和鄂畢烏戈爾人,都位於此地。
第四階段——象徵性使用。這是真正的薩滿教階段,當麻醉藥品僅被視為符號時,它們在功能上被迫脫離儀式實踐進入家庭消費領域,在那裡它們成為節日(改變的)社會狀態的一個屬性。必須假設這些階段發生在古代,或者仍在進行,所有藥物都為傳統文化所熟知[4]。
又是鵝膏菌。
基於上述假設,西伯利亞人民認為飛木耳是強大的精神,他們與下層世界的聯繫以及與他們接觸並通過他們與一般精神世界接觸的可能性,通過吃蘑菇,是很可能是純粹的原型,在遠古時期由於食物或藥理測試、巫術實踐的發展以及前薩滿教級別的儀式和儀式活動過程中的幻想實驗而形成。然後,我們只能在魔法儀式的背景下談論考古發現中的蘑菇形象(當然,如果它們是蘑菇的話),順便說一下,集體接受致幻劑和聯合舞蹈是可能的,這是許多人想要的在岩石雕刻中看到。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可能將食用木耳的儀式傳統與臭名昭著的索瑪嚴肅地聯繫起來(我個人非常懷疑),那肯定不能通過薩滿教,在薩滿教中,藥物的使用被指定為象徵意義。事實上,仔細觀察後,飛木耳蘑菇不是巫術,而是魔法。
文學:
Karjalainen KF Die Religion der Jugra - Volkern。赫爾辛基,1927 年。三、
Lehtisalo T. Entwurf einer Mythologie der Jurak-Samojeden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 - Ougrienne。赫爾辛基,1927 年。 53.
Levi-Strauss C. Levi-Strauss C. Les champignons dans la culture // L`Homme。 1970 年第 10 頁,第 5-16 頁。
Wasson RG Soma:不朽的神聖蘑菇。 - 海牙,木桐,1968 年。 - 380 頁。
Wasson RG,Wasson 蘑菇、俄羅斯和歷史副總裁。 — 紐約,Pantheon Books,1957 年。2 v。 — 432 頁
Astakhova V. G. 有毒植物之謎。 M.:木材工業,1977 年。第 1 部分。有毒植物。
Bogoraz VG 楚科奇人的物質文化。 M.:科學。 1991. - 224 頁
Bogoraz-Tan V. G. Chukchi。第二部分。宗教。 L .: 北海航線負責人出版社。 1939. - 208 頁
Bongard-Levin G.M., Grantovsky E.A. 從斯基泰到印度。 M.:思想。 1983. - 206 頁
Brekhman II, Sem Yu. A. 西伯利亞和遠東人民的某些精神活性藥物的民族藥理學研究//遠東藥物。哈巴羅夫斯克,1970 年。問題。 10,第 16-19 頁。
Butanaev V. Ya. 哈卡斯民族文化。阿巴坎:哈卡斯出版社。狀態大學1998. - 352 頁
Garkovik A.V. 小塑料製品反映了古代社會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遠東的古代圖像世界。太平洋考古學。第 10 期。符拉迪沃斯托克:FEGU 出版社。 1998. S. 49 -58。米。 1;5。
Georgi I. G. 描述了居住在俄羅斯國家的所有民族,他們的日常儀式、習俗、服飾、住所、鍛煉、娛樂、宗教和其他紀念物。聖彼得堡,1799 年。第 1-4 部分。
James P., Thorp N. 古代發明。明斯克:花香。 1997. - 768 頁
Dikov N. N. 東北亞古代文化。古代亞洲與美洲的交界處。 M.:科學。 1979. - 352 頁
Dikov N. N. 古代楚科奇的岩石之謎。 Pegtymel 的岩畫。莫斯科:瑙卡出版社,1971 年。
測量員 F. Elistratov 的白天紀念館,從沿著 Penzhina 灣海岸的 Tagal 堡壘到河流。 1787 年 9 月 14 日至 21 日,在名義顧問 Bazhenov 的指揮下的 Penzhins // 1785 年至 1795 年東北地理考察的民族志材料。馬加丹:馬加丹書。出版社,1978 年。
Devlet M.A. 來自葉尼塞薩彥峽谷的古代擬人圖像 // 西伯利亞古代文化與鄰近地區文化之間的相關性。新西伯利亞:Nauka,1975 年,第 238–248 頁。
Devlet M. A. Dancing little men // Priroda,1976 年。第 9 期,第 115-123 頁。
Elizarenkova T. Ya., Toporov VN 關於蘑菇的神話思想與 soma 的原始性質的假設有關 // IV 暑期學校關於二級建模系統的摘要。塔爾圖,1970 年,第 40-46 頁。
Kiryak M.A. 西楚科奇舊石器時代晚期圖形(移動藝術紀念碑)情節中的蘑菇//遠東古代圖像的世界。太平洋考古學。第 10 期。符拉迪沃斯托克:遠東國立大學出版社,1998. S. 106 - 122。
Kiryak (Dikova) 文學碩士遠東北部的古代藝術(石器時代)。馬加丹:SVKNII FEB RAN,2000 年。- 288 頁。
Krasheninnikov S.P. 對堪察加半島的描述。 M., L.:Glavsevmorput 出版社,1949 年。
Kulemzin VN, Lukina NV 認識漢特人。新西伯利亞:Nauka,1992 年。- 136 頁。
Makkena T.眾神的食物。 M.:超個人研究所出版社。 1995. - 379 頁
Meletinsky E. M. 古亞洲人的神話//世界人民的神話。 M., 1988. T. II.第 274-278 頁。
Okladnikov A.P. 下安加拉(從 Serovo 到 Bratsk)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新西伯利亞:Nauka,1976 年。- 327 頁。
Okladnikov A.P., Zaporozhskaya V.D. Transbaikalia 的岩畫。 L.: Nauka, 1969. 第一部分。 — 217 頁
Okladnikov A.P., Zaporozhskaya V.D. Lena 中部的岩畫。 L.: Nauka, 1972. - 271 p.
Patkanov S. 根據 Ostyak 史詩和英雄傳說的 Ostyak 英雄類型。 SPB,1891 年。
Podmaskin VV Udege 對藥用植物和動物的使用 // 東亞和東南亞的生物資源及其使用。海參崴:Nauka,1978 年,第 54-60 頁。
Spevakovsky A. B. 阿伊努人的精靈、狼人、惡魔和神靈(傳統阿伊努社會的宗教觀點)。 M.: Nauka, 1988. - 205 p.
Tivanenko A. V. 布里亞特古代岩石藝術。新西伯利亞:Nauka,1990 年。- 206 頁。
Toporov V.N. 蘑菇 // 世界人民的神話。 M., 1987. T. I. C. 335–336。
Troitskaya T. P., Borodovsky A. P. 鄂畢森林草原地區的 Bolsherechenskaya 文化。新西伯利亞:Nauka,1994 年。-184 頁。
Formozov A. A. 關於蘇聯石刻的新書(1968-1972 年出版物回顧)// SA,1973 年。第 3 期
Chernetsov V. N. Vogul 的故事。滿西族民俗文集。 L., 1935.
Shatilov M.V. Narymsky 地區的 Ostyako-Samoyeds 和 Tunguses // 托木斯克當地傳說博物館的論文集。托木斯克,1927 年。T.I.
Eliade M. 薩滿教:迷魂藥的古老技巧。 M.: Sofia, 1998. - 384 p.
注意事項:
在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中使用蘑菇的科學
不一致 pl。和單位這些數字是引用作者的錯誤。
這裡可能有點誇張,超過七個蘑菇的劑量是劇毒的,可以致命。
回想一下,現代吸毒成癮與使用傳統文化的精神藥物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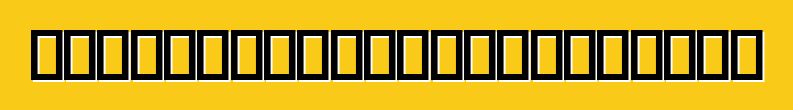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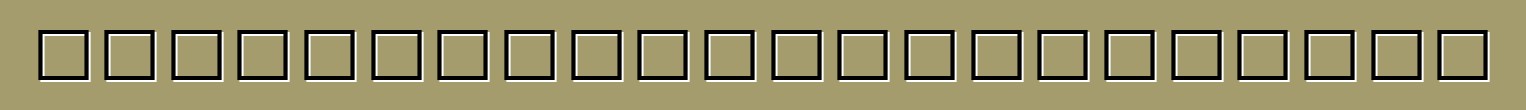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50:53 +0300 GMT
0.003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