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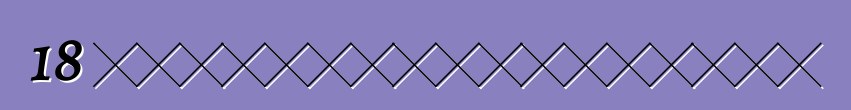



最早的歷史和民族志資料,除其他外,為我們提供了有關西伯利亞人民薩滿教的信息,但尚未窮盡,也未得到充分研究。通過仔細研究,並在必要時進行語言處理,這些材料可以成為真正獨特的信息來源。這裡的一個例子是 Evenks 和 Evens 薩滿教的材料,這些材料是 18 世紀 40 年代由 J. I. Lindenau 在鄂霍次克海岸收集的——這些文本以德語手稿的形式提供給研究人員,1983 年,它們被翻譯成俄語出版然而,即使在那之後,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沒有引起精神文化專家的注意[1]。在仔細研究 J. I. Lindenau 在舉行儀式時直接用原始語言寫下的文本後,從 Lindenau 的材料中提取了一些與幾個儀式相關的 Evenki 儀式法術,以及整個薩滿教儀式Even 語言,出於不明原因,作者將其放在專門描述烏德斯克監獄通古斯人(Evenks)的部分中。據我們判斷,這種儀式為研究人員提供了一種薩滿精神的百科全書,它反映了這些精神按列舉順序排列的等級制度,也使確定薩滿可以了解哪些超自然生物成為可能。執行儀式時的地址[2]。
這部作品的主題是歷史和人種學來源,提供有關鄂溫克人的信息,指的是 1789-1790 年。這就是所謂的“托博爾斯克省描述”[3],是對西伯利亞某個行政單位的綜合描述。根據標準調查問卷編制,“描述......”詳細描述了領土的自然和氣候條件、自然資源和礦產、定居點以及人口的種族構成、職業、生活和文化這個領土的。關於“托博爾斯克州州長描述”所涵蓋的領土,其主題是“Ostyaks”(漢特)、“Samoyadi”(涅涅茨)、“通古斯”(Evenks)和雅庫特。儘管《描述》發表已近20年,但在處理鄂溫克人的精神文化問題時,還沒有引起民族志學家的注意。與此版本一起,忽略了 197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版的關於 18 世紀西伯利亞人民民族志的兩個更有價值的資料來源,將它們作為“描述”信息的比較或補充材料非常有趣托博爾斯克州長”。這份“描述……”包含真正獨特的材料和關於鄂溫克人物質和精神文化的寶貴信息。除了服裝、職業、家庭和婚姻規範以及宗教信仰等標準特徵外,描述還包含有關 Evenk 文化某些方面的獨特信息。例如,其中包括對 Evenk 狩獵的詳細描述 [4]。
我們關注的直接主題是“托博爾斯克總督職位描述”中專門介紹鄂溫克薩滿教的那些片段。除了“描述……”作為一個新的、以前幾乎不為人知的事實材料來源的不可否認的價值之外,這個來源在系統化編譯器的觀察方面具有相當大的意義。一位不為人知的觀察者對鄂溫克人的薩滿儀式進行了描述,不僅向我們展示了鄂溫克人薩滿服飾的特點、薩滿祭祀儀式的目的和主要特點。正如我們可以判斷的那樣,與他同時代的許多旅行家和研究人員不同,這篇“描述……”的作者成功地深入了解了Evenk 薩滿儀式的許多基本特徵。他的注意力並沒有逃避薩滿行為的這些特徵,例如薩滿與執行儀式的動機相關的一種表演遊戲、狂喜狀態的模仿性質,以及人們可能會說的特殊符號表現鄂溫克薩滿在幾個儀式的表演中實現的世界觀思想。
“描述……”是這樣描述薩滿儀式的動機、薩滿的衣服和執行儀式的:他會召集人們,穿上帶有特殊飾品和徽章的鎖子甲,徽章上有蛇頭,敲著手鼓,在火邊奔跑,大喊“goy”,“goy”,站著的人也跟著他,然後,睜大眼睛,倒在地上,喘息,從公司噴出泡沫,一段時間後起床,四處張望,打哈欠 butto 是多麼瘋狂,然後他站起來告訴在場的人,魔鬼帶來了(問?)這樣那樣的犧牲,這是給定的。當然,這裡對帶有大量金屬元素的薩滿“鎖子甲”服裝的詳細描述很重要——從民族誌類比可以判斷,很可能是帶有金屬飾牌和漏斗形吊墜的服裝,出現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服飾上。薩滿衣服上蛇(“蛇頭”)圖像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因為蛇崇拜在鄂溫克薩滿教中的存在遠非顯而易見。文本中同樣重要的評論是薩滿的個人、純粹的物質利益作為執行儀式的動機或理由——儘管據推測,這並不是執行儀式的唯一原因和理由。特別有意思的是,根據“描述……”的文字,觀察者眼中薩滿巫師在薩滿教化過程中的狂喜絕對是虛幻的(“彷彿他在一個偉大的狂熱”)。
與其他來源相比,有趣且新穎的是 Evenk 薩滿教儀式的介紹,該儀式旨在幫助婦女分娩:“當一名婦女在分娩時長時間遭受痛苦時,薩滿會砍下一個殘肢,將楔子敲入其中,為了迅速解決這個負擔,他們不斷地從與薩滿在一起的人那裡無意中聽到他們在蒙古包裡告訴對方她快要生了,或者還沒有。在那之後,楔子或多或少地被敲打,薩滿為生下的嬰兒命名,但它是那個家庭的新嬰兒“[6]。很難懷疑觀察者沒有註意到同情魔法的元素在他所考慮的薩滿巫師的行為中。薩滿教的本質特徵是外部觀眾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些在薩滿教期間扮演次要角色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靠近蒙古包的人扮演這個角色——他們告訴巫師觀察分娩婦女的狀態,從而不僅允許巫師在分娩時調整他用樹樁和楔子進行的魔法操作,而且他們還親眼觀察巫師力量的所有超自然力量,體現在儀式中。關於用“shtob 是那個家庭的新成員”這個名字命名新生兒的評論也很有價值。即使在今天,也禁止給新生兒起他們年長親戚使用的名字,如果他們仍然我們還活著。直到 20 世紀 30 至 40 年代,楚科奇人一直保留著傳統的名字,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給孩子取名字的方式,他們習慣給新生兒起一個名字,這個名字是其中一位親戚的修改後的名字,如果他還活著:既然很多楚科奇人的名字都是複合詞,那麼人名的修改並沒有造成困難。這種習俗的一個遺跡是楚科奇姓氏的保留,可以追溯到個人名字,許多名字包含相同的詞根,例如,vykvyn 'stone,' y'ttyn 'dog' k'ora-n "s “鹿”、“可樂”、“惡靈”、“惡魔”等,由此可以形成幾十個名字。事實上,薩滿給新生兒起名,我們可以假設一種倖存的習俗形式。確定哪些已故親屬以這個嬰兒為幌子回到了活著的人的世界,這源於通古斯人特有的輪迴觀念。
“托博爾斯克州長職位描述”的其中一個片段描述了與擺脫傳染病相關的幾個連續執行的薩滿儀式。這是這個片段:“在 Chepogirey(Evenki 氏族 Chapogir - A.B.)之前,有多達一千人,但在以下案例中,許多人死於天花。其中一個被阿馬納特帶到葉尼塞斯克市一年,這在當時由於經常發生騷亂是必要的。他染上了天花,逃回鄉里感染了。與此同時,有一位光榮的薩滿巫師承諾將他的兄弟從天花的惡行中解救出來。他在一棵非常粗的樹上鑽了一個洞,這樣一個人就可以從裡面爬出來,然後薩滿會在那一刻把洞堵上,這樣天花就會留在樹的另一邊,所以猶豫著讓一個接一個地去。之後,他開始薩滿化,並轉向所有人,他說沒有辦法解脫自己,我們都會迷路,但他還下令徹底建造一個帶有內部穹頂的土丘,以便人可以爬過去,他對一棵樹進行了同樣的儀式,但即使這樣也無濟於事。薩滿衝進 Podkamennaya Tunguska 河,緊隨其後的是其他人,有些人騎著鹿,像女人一樣游泳,他們的肚子在水流中死去,還有一些人無法離開多岩石的河岸,儘管在那個地方河不寬。又有一小部分出去留在岸上的人逃得更遠,從而得救了。
毫無疑問,對於講述薩滿試圖擺脫天花的故事的觀察者來說,指導薩滿實踐的意識形態和符號學理念變得顯而易見。這個片段始終如一地描述了薩滿如何試圖將他的親屬從傳染病中拯救出來,如何連續三次執行克服障礙的儀式,這些障礙是創造或選擇的,以便移動到疾病無法進入的另一個空間領域。第一次是樹幹上有洞的樹 - 一種自然物體障礙和屏障中人工通道的組合,第二次 - 帶有拱頂的人造土墩,或完全人造的屏障,第三次被不同部分空間之間的障礙所克服,作為一個完全自然的地理對象——河流。在這個來源的文本中,薩滿執行的儀式中穿過障礙的功能符號學意義如此明顯,以至於觀察者顯然無法注意到薩滿“劃定”空間的行為的真正含義,以便獲得擺脫疾病,以及屏障的象徵意義,這是 M. Eliade 寫下的靈感[8]。根據這段文字,很難說過河是純粹的傳統意義,還是與醫學或生態知識有關,但毫無疑問,巫師發明並強迫他的前兩個動作親戚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助長了傳染病的傳播。目前尚不清楚遷移期間集體渡河是否是擺脫傳染病的手段,以及將這種習俗歸因於鄂溫克人的傳統醫學知識是否合理。
這種薩滿儀式對於醫學薩滿實踐(與患者治療相關的儀式)的研究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因為它在對可追溯到 18 世紀和近現代的薩滿祭司行為的描述中有類比. Y. I. Lindenau 在死後一年安排的紀念活動中描述了鄂霍次克沿岸 Evenks 薩滿的類似行為:J. I. Lindenau 將這種儀式描述如下:閱讀 - A.B.)。他們拿一塊爛木頭,因為它很軟,可以砍斷,他們用它做了一個木頭,應該代表死者。他穿好衣服,放在寡婦或鰥夫睡覺的床上。之後,其他住所的鄰居會帶來最好的食物。馴鹿立即被勒死,肉被煮熟,與所有其他食物一起提供給笨蛋。之後,一位巫師拿著手鼓過來開始唱歌。他每頓飯都拿一塊,把木頭送進嘴裡,然後又拿走,自己吃,抽煙斗,對著木頭吐煙。之後,大家開始吃飯,把店裡的東西都吃光。吃完飯,薩滿又開始念經,最後他們給他拿來一條內臟,在場的所有人都從裡面爬過去。在那之後,薩滿用寫給笨蛋的話來切割它:Asillahujiatept Oekelmuntschanra, nowirackel, oekelnowira Mutschanadi, hutalningira。在俄語中,這意味著:“看夠了,夠了,不要回來,不要破壞我們的狩獵,不要傷害你的孩子!”
薩滿說了這話,衣服就從木頭人身上撕下來,一個人拿走,把它帶出住所,掛在樹上,或者像一文不值的東西一樣扔掉。之後,死者對追悼會一點也不滿意”[9]。我們這樣閱讀這個儀式的文本:Esille (=ekellu) kojetmette, ekel mucunra, nejir ekel, ekel nejir mucunda, hutel ningira。閱讀文本的翻譯如下:“不要看對方,不要回頭,不要再回頭,不要再回頭,孩子們召喚”[10]。一種類似的儀式,根據執行它的人的觀點,能夠擺脫流行病,在楚科奇人中存在:人們在一個由棍子製成的外表下的拱門下通過的儀式,上面有狗的內臟被掛起,直到 30 年代末,由楚科奇阿納德爾地區的楚科奇人保存,作為防止流行病的一種手段(作者的現場筆記:Ivtek Unukovich Berezkin 的通訊,生於 1929 年,瓦扎苔原人) .同樣儀式的迴聲也保存在上科雷馬尤卡吉爾人的民間傳說中:一位薩滿將一位老婦人——病魔引誘到屋子裡,用狗腸包裹它;老太婆,病靈,不能離開房子,之後人們永遠離開這個地方[11]。
“托博爾斯克總督職位描述”材料的作者為我們提供了埃文克薩滿的行動及其活動的幾乎詳盡的畫面。上面,我們已經註意到巫師在分娩時的幫助以及巫師從流行病中解救出來的方法。 “描述......”的材料還包含了與預測未來相關的鄂溫克薩滿行動的描述 - 鄂溫克薩滿和埃文薩滿以及遠東北地區人民薩滿的通常目的地。在談到鄂溫克人的信仰時,他指出,鄂溫克人“有薩滿而不是祭司,他們受到他們的尊敬,他們是被預言的,這對他們來說幾乎經常成為現實,他們擁有強大的代理權。什麼預言,聚成一團,中間生火。每個人都會盤腿坐下,彎下腰,看著火光。此外,他們唱歌和打手鼓。過了一會兒,巫師站起來,開始在火堆附近以各種方式跳得很高,同時不斷地把一個扔進火裡,另一個則鑽進地裡。他們隱身了很短的時間,但在座的人只聽到一個聲音,然後他們再次出現在觀眾面前。然後,背負著掛著的鐵牌匾和塗鴉,瘟疫隨著煙囪跳出來,在街上稍作停留後,又從同樣的煙囪或門進來。累了,重量,躺在地上,好像昏厥一樣休息,他們恢復知覺後,開始唱歌並呼喚他們死去的親戚,他們曾經是這樣的巫師。然後他告訴坐著的人他的所見所聞,他們每個人以及一般人的想法”[12]。
在這種描述中,與那些帶有預測未來的薩滿儀式的民間傳說材料相比,這些民間傳說材料包含薩滿對未來的願景的呈現文本[13],儀式的純粹視覺方面在民間傳說描述中是不存在的, 非常有趣(這是可以理解的:民間傳說文本是針對那些已經很熟悉預測未來的薩滿教實踐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執行旨在預測未來的儀式時,薩滿可以去上層世界(即從煙孔中跳出),或去下層世界(“其他人進入地下。”)薩滿可以將自己投入火中的信息顯然也指薩滿尋求的事實“看到”上層世界的未來:在這裡,“描述......”的作者觀察者似乎是整個觀察薩滿行為的唯一一次,他成為薩滿催眠的受害者。封閉的房間瘟疫,中間有火在燃燒-這在對正在考慮的預測未來的儀式的描述中以及首先考慮的描述的片段中都有說明,並且據說薩滿巫師在與輔助神靈交流時,“繞著火跳”。很明顯,住宅的封閉、半黑暗的空間,觀眾所在的地方——薩滿儀式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顯然,沒有觀眾的薩滿活動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因為薩滿實踐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變成了巫術),以及照亮“場景”和主要演員薩滿的明亮火光,在儀式中是一種在觀察者中產生催眠或類似催眠效果的手段,類似於舞檯燈光所產生的效果在現代劇院的觀眾席上。至於薩滿服飾的特點,其上的“空白”,即薩滿的輔助神靈圖像,在這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果在“描述”的第一個被考慮的片段中,蛇的圖像作為薩滿服裝的一個元素出現,那麼在這篇文章中,薩滿的靈魂助手具有擬人化的特徵。顯然,鄂溫克薩滿巫師的靈魂助手兼具擬人化和動物化的特徵;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Evens 中,然而,在後者中,以薩滿服飾和其他薩滿屬性的圖像形式,擬人化的人物占主導地位,其服裝的季節性和種族不同。一個有特色的細節是巫師對已故親人的祈求,而巫師顯然也是巫師的助手,而“誰以前是這樣的巫師”這句話顯然可以證明巫師在巫術過程中向死者的親屬求助。那些擁有最大程度薩滿天賦的死去的親人。
至於薩滿在儀式中的跳躍,讓他通過煙孔離開了帳篷,在這裡,據我們判斷,無論對現代研究人員來說有多麼奇怪,我們都必須完全相信這個介紹。從人種學和民間傳說材料中,我們知道通古斯人(伊文斯人和伊文克人)和遠東地區人民的戰士必備技能之一是能夠通過煙洞跳出住所[14] ]. “halkamchali melun”chin 的表達 - “從住宅的上部開口跳出,支撐桿 - halkamcha 十字架”經常出現在鄂霍次克海岸 Evens 的故事和傳說中。因此,在這裡,在鄂溫克人的薩滿儀式中,實現了一個完全平淡無奇的細節,涉及體育鍛煉和軍事事務的實踐,絕不是觀察者的發明或自欺欺人的神奇財產。
作為歷史和人種學來源,“托博爾斯克總督轄區描述”在 18 世紀其他包含西伯利亞人民精神文化信息的類似文件中脫穎而出,在信息量和可靠性方面毫不遜色.類似的來源——“伊爾庫茨克州長的描述”,於 1792 年編譯,也是最近才出版的,包含的關於鄂溫克人和西伯利亞其他民族的薩滿教的信息要少得多,而且他的一些信息涉及其他民族,而不是本文中提到的文檔。因此,它說:“科里亞克人也非常尊重地崇拜太陽和月亮,此外,他們沒有偶像,而是掛著鹿皮的人骨”[15]。此處提到的保留死去薩滿巫師骨頭的習俗只是尤卡吉爾人的特色。此處使用民族名稱“Koryaks”顯然是錯誤的,並且是基於其內部形式。在楚科奇語中,ak "oraki, ak" oraki-lyn 的意思是“沒有鹿,沒有鹿”,這個詞適用於任何以馴鹿牧民為代表的民族,最初用於與楚科奇濱海邊疆區有關,後來- 定居的濱海邊疆區科里亞克人。 I.K. Kirilov 早在 18 世紀中葉就知道所描述的習俗是 Yukaghirs 的典型習俗:“[16]。 《伊爾庫茨克總督轄區記述》中的另一段報導說,在通古斯人(埃文克斯)中,“古代偶像拉克米亞、日金多爾或迪加雷多、古凱利斯、阿拉萊、古納拉亞的名字至今未被消滅”[17]。從上下文來看,本“描述”的編者採用了與鄂溫克人的異教信仰有關的名詞的給定詞。然而,很明顯,這裡的觀察者誤認為神的名字——“古代偶像”要么是薩滿舞蹈的呼喊,要么更可能是一些詞,是 Evenk 圈子的吟唱詞舞蹈“Ekhorye”。
托博爾斯克省描述中包含的有關 Evenki 薩滿教的信息將此來源與 18 世紀西伯利亞人民民族志的其他材料區分開來,作為一份獨特的文件,與事實部分一起,也提出了觀點觀察者的。與他那個時代的許多旅行者和科學家不同,“托博爾斯克州政府描述”的編纂者能夠充分評估鄂溫克薩滿儀式的戲劇性和壯觀的組成部分,而這些部分仍然沒有被俄羅斯人民文化的研究人員看到西伯利亞很長一段時間。非常有價值的是關於薩滿操縱可以基於薩滿的個人物質利益的報告,這使本文更接近 S.P. Krasheninnikov 早期對堪察加人民薩滿實踐的觀察:[Koryak - A.B.]薩滿名叫 Karymlyach,他不僅當地的異教徒,而且哥薩克人都被尊為偉大的鑑賞家,尤其是因為他用刀刺自己的腹部並喝他的血: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嚴重的欺騙,任何人都可以注意到,如果有沒有被迷信蒙蔽雙眼的人。他先是跪著打了一會兒鈴鼓,然後又拿刀往自己的肚子上紮,用手不在的手把傷口的血引出來,最後拖出一大把血從他的皮大衣下面,舔著手指吃掉了它。同時,我笑得很厲害,他對業務的了解如此之少,以至於他在學校也不適合我們的大劇院。他假裝用來刺向自己的刀,將他的腹部放低,從他胸下的膀胱中流血。對這一來源特別感興趣的是對為消除天花而進行的薩滿儀式的描述,其符號學意義對於“描述......”的作者來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以至於他能夠表達它在他的文本中,以及具有強調“戲劇”特徵的薩滿儀式的一些特徵。在評論“托博爾斯克州長的描述”的片段時,還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某些類型的鄂溫克人和西伯利亞其他民族的薩滿教儀式必然需要觀眾在場,並且他們的表演沒有明顯的意義在場的人數顯然沒有意義。
對“托博爾斯克州長的描述”一文的研究,這被證明是西西伯利亞人民民族志的一個非常有用的來源,以及其他可以參與西伯利亞薩滿教研究的文件,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關於 18-19 世紀北方、西伯利亞和遠東人民歷史和文化的早期資料不僅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且還遠未窮盡。即使在今天,這個地區仍有可能有真正的發現。
總結:
A. A. 布里金
十八世紀俄羅斯觀察家眼中的通古斯(鄂溫克)薩滿教。
這篇論文的主題是十八世紀俄羅斯觀察家所描述的通古斯 (Evenki) 薩滿教。該論文以十八世紀的文件為基礎,對西伯利亞不同地區的一般描述進行了描述,這些描述最近才出版,但仍未被視為了解遠北地區人民歷史和文化的重要信息來源,西伯利亞。文中分析的文獻片段包括薩滿服飾及其配飾的圖片,以及一些薩滿教儀式,其中包括薩滿在分娩期間對婦女的幫助,薩滿為擺脫傳染病而進行的活動,以及旨在為未來提供服務的儀式。除了對巫師實踐的描述之外,本文中正在分析的文件還為我們提供了與觀察者的觀點和作者對巫師行為的個人看法相關的信息。這篇論文的試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溫克薩滿祭祀儀式中的視覺戲劇成分,200 年前的觀察者註意到並正確理解了這一點。
注意事項:
林德瑙亞,我。西伯利亞人民的描述(18 世紀上半葉)。馬加丹,1983 年。
Burykin A. A. Ya. I. Lindenau 筆記中 18 世紀通古斯卡薩滿法術 // 西伯利亞和北美古代文化之間關係的系統研究。問題。 5. 聖彼得堡,1997 年,第 129–135 頁,第 139 頁。
托博爾斯克州的描述。新西伯利亞,1982 年。
托博爾斯克州的描述。第 239 頁。
那裡。第 226 條。
那裡。第 225-226 頁。
那裡。第 226-227 頁。
Eliade M. 神聖而平凡。莫斯科,1994 年,第 24-27、112-115 頁。
Lindenau Ya. I. 西伯利亞人民的描述。第 91 頁。
18 世紀的 Burykin A. A. Tunguska 薩滿法術 ... S. 127–128。
參見:地球之主。森林Yukagirs的傳說和故事。雅庫茨克,1994 年。第 28 頁。
托博爾斯克州的描述。第 237-238 頁。
例如,參見 Kormushin I.V. Udykhey (Udege) 語言。 M., 1998. S. 115-116,文本 N 7-“七個食人者”。薩滿預言未來的一小部分也包含在 Even 史詩故事之一中(Lebedeva Zh.K. 遠北人民的史詩紀念碑。新西伯利亞,1982 年,第 103 頁)。
參見:Novikova K. A. Even 語言方言論文。動詞、功能詞、文本、詞彙表。 L., 1980. S. 133, 143. 書中同:連童話、傳說和傳說 / Novikov K. A. Magadan 編譯,1987. S. 102。
伊爾庫茨克副省的描述。新西伯利亞,1988 年,第 155 頁。
Kirilov I.K. 俄羅斯國家的盛開狀態。 M., 1977. S. 296。
伊爾庫茨克副省的描述。 1792 年,第 217 頁。
Krasheninnikov S.P. 對堪察加半島的描述。 T.2. SPb., 1755. S.158–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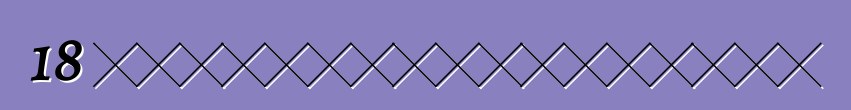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51:17 +0300 GMT
0.010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