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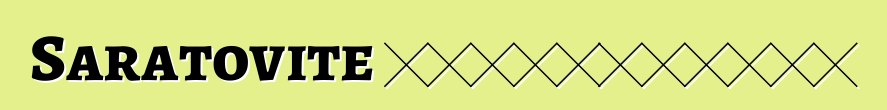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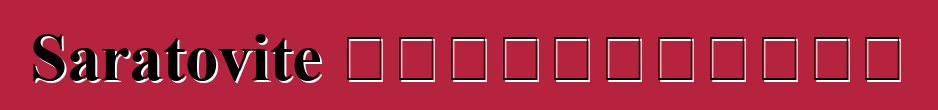



薩拉托夫。 Taras Zhurba 是一名薩滿。雖然看不出來:時尚青年,走地球,坐公交,寫“肥皂”。在成為魔術師之前,塔拉斯完成了他的哲學論文答辯,當過敲鐘人和政治公關人員,差點進了一座修道院,學習了西藏瑜伽和卡斯塔內達的托爾特克魔法系統。你不能僅僅因為你想成為薩滿。真是緣分啊選擇伴隨著一種不幸的副作用,稱為薩滿疾病。小時候,塔拉斯有過非凡的經歷:“我醒來時問自己:我在哪裡?房間裡坐著一個人——一件毛茸茸的、難以理解的繡花襯衫,腋下繫著一條腰帶。奇怪的生物出現了,撕開我的肚子,把它們的食物放在那裡。我意識到這樣生動的夢不會發生。我想,這個夢想和現實有什麼區別?父母(演員媽媽,工程師爸爸)沒有問深奧的問題,他們使用的是沒有幫助的常規藥物。在 90 年代初的大學裡,每個人都在尋找真理。
仔細閱讀未來教科書的生動頁面是一種令人興奮的體驗。歷史專業的學生尤其感受到這一點。當時正在瘋狂運轉的社會電梯,載著歷史系的畢業生們前往各個方向。塔拉斯沒有選擇回報最快的行業——哲學。有一次,他應一位垂死的信徒祖父的要求,來到聖三一大教堂接受洗禮。並在鐘樓度過了五年。塔拉斯說:“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當你連續四五個小時拜訪復活節時,靈魂就會暴露無遺。”“人們強烈需要宗教,需要一個能為我開路的人。” Zhurba 前往 Mordovia,前往 Sanaksar 修道院,以接受命運和道路的指示,並在必要時繼續出家。 Schiegumen Jerome 回答了這個未被問到的問題,並祝福他能看得更遠。在薩拉托夫官邸,朱爾巴在一次演講中遇到了喇嘛奧萊尼達爾。他在修道院的祈禱中加入了佛教冥想。
大學的研究生並沒有遠離世界。他為關於權力哲學和人類動機的本質(包括如何吸引公民到垃圾桶)的論文辯護。參加了州長 Ayatskov 的第一次競選活動,在莫斯科政治諮詢中心“Nikolo-M”工作。塔拉斯說:“我探討了是否有可能參與政治並成為一個誠實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同時在精神上實現自我。”“很明顯,沒有老師這是不可能的。”
夢表明這個人一定是薩滿。在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塔拉斯會見了被稱為“圖瓦研究鼻祖”的塞維揚·范斯坦教授。韋恩斯坦先生建議薩拉托夫市民訪問克孜勒。莫斯科出版商將這個年輕人送到了那裡(塔拉斯試圖出版一本關於人類在歷史終結時的命運和對世界末日主題的反思的書)。出版社拒絕印刷這篇文章,並建議“在卡斯塔內達手下寫作”:他們說,一個俄羅斯人最終去了西伯利亞,找到了一個本地人唐璜,並在文中進一步說明。 “如果你已經在寫作,那就真的,”Zhurba 決定並開車離開了。
去圖瓦並不容易。火車不去這裡,因為沒有鐵路。可以從阿巴坎乘飛機或駕車穿過東薩彥嶺到達。 “在薩揚人之前,周圍的一切都是熟悉而明顯的:這裡的白樺樹多一點,那裡的山多一點。在第二遍之後,現實感知的焦點發生了變化。從上面看有一種圓頂的特殊感覺。你自己的身體變輕了。否則,時間流逝,更多的意義出現在日常事件中。在圖瓦,一切都比我們小,但更有活力。人的個頭更小,封印的生命力更多。我們又大又松。他們壓抑、狂暴又開朗,”塔拉斯說。克孜勒(意為“紅色”)約有 100,000 名居民。這裡是地球的肚臍,是大小葉尼塞河交匯處的一個地理點,與亞洲大陸的大陸線等距。這座城市類似於任何區域中心,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在列寧街上盤旋的不是鴿子,而是獵鷹。在 Lenina,41 有一個薩滿教中心“Dungur”,教義的代表在那裡接待來訪者。參觀者眾多,形形色色。也有很多巫師。小屋的外牆上掛著邀請標誌,院子裡矗立著儀式用的蒙古包。有五到十個薩滿教組織,200 多人(共和國全部 30 萬居民)。諮詢薩滿不是遊客的“小玩意兒”。為了尋求幫助(在生病、孩子出生、狩獵開始之前等),土生土長的圖瓦人也會求助於他們,這是很常見的事情。但由於對宇宙結構的濃厚興趣,當地居民尊重巫師、牧師和喇嘛。此外,城裡還有瑜伽士、幾位通靈師、進行放血療法、骨按摩等的傳統治療師。
“在 80 年代後期,中央的補貼停止了。共和國幾乎不生產任何東西。經濟崩潰,圖瓦淪為某種國家的附庸。他們如何仍然生存是一個謎。大概是薩滿天賜的福氣吧。幸運的是:人們的穿著不亞於莫斯科,街上有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國汽車。 “牛仔夾克的口袋裡有一個筆記本和一支筆。他表現得像個愚蠢的卡洛斯·卡斯塔內達:他四處走動,提出問題,然後把一切都記下來,”塔拉斯回憶道。他介紹自己是一名為論文收集材料的科學家。繞過30-40“專家”。兩個“經驗豐富的騙子”成功地揮霍了。 “一年後,我意識到他們利用了我的弱點。你怎麼咬的?其中一位自稱 Aldincha,意思是“金箭”。這是一個女性的名字。”
根據 1937 年的人口普查,每 80 名居民就有一名薩滿。來自雅庫特、哈卡斯、布里亞特和阿爾泰的僕人來到圖瓦學習。 1944 年,在自願吞併後,圖瓦有 3,500 名巫師被槍殺(儘管他們歡迎蘇維埃政權、集體化,並為衛國戰爭的勝利舉行儀式)。屠殺現場,被視為療傷的阿爾贊九噴泉開始跳動。偉大的巫師說他們的時間到了並離開了這個世界。據目擊者稱,他們被捕時在一個封閉的蒙古包裡消失了。但不是所有的。偉大的巫師科克納恰蘭支持葉尼塞柯爾克孜人起義的參與者,死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監獄。正如他們所說,他死後散發出狼的能量,懲罰了數十名最熱心的告密者和人民戰士。年輕巫師的培訓系統和一種“質量控制”被摧毀了。倖存的專業人士躲藏起來。根據朱爾巴的說法,共和國的農村地區現在還留有兩三個白人薩滿老巫師和幾個有天賦的孩子。由於他們的年齡,他們和其他人都沒有進行廣泛的實踐。
塔拉斯確切地知道他生命中的哪一天是最快樂的——1997 年 8 月 24 日。 Tash-ool Buuevich Kunga 不小心駛入了 Dungur(“tash”是硬的意思,“buu”是子彈的意思,“kunga”是快樂的意思)。他成了薩拉托夫的老師。 “我在這個人的眼中看到了無底智慧的光芒,非常嚴厲和仁慈。我覺得我認識他已經無限久了。但是為了匹配交流的水平,我需要不斷地跳出褲子。 Zhurba 直接問對話者:“突然間你也在說謊?”。作為回應,Tash-ool Buuevich 講述了這個年輕人的簡短傳記,並描述了他口袋裡的東西。
Tash-ool Buuevich(第四代白人巫師)出生於鐵龍年(1940年)。一個五歲的男孩被認為是一份獨特的禮物。 Tash-ool Buuevich 改變了許多職業。曾任林務員。 “在圖瓦,一種野蠻的偷獵方法很普遍:針葉林被點燃,部分場地被燒毀,整個地塊被交給“衛生”砍伐。老師通過下雨來滅火。有一次,他的大兒子走得太遠了,七月份就下雪了,”塔拉斯說。 1987年,Tash Buuevich在蘇聯圖瓦舉辦了第一次薩滿研討會(按照傳統,同事們每六個月要開會交流經驗)。貢噶在埃爾津的薩馬加爾泰建造了佛教寺廟,並創立了巫師組織“Kuzungu-eeren”。他的第一個學生是肯·海德先生,他是倫敦人,蘇格蘭場的記者。
薩滿入會儀式沒有電影價值。它根本不會發生在這裡。正如塔拉斯所說,在睡覺之前,老師帶他去了精神世界(九重天),並在告知了召喚後,把他留在那裡——自己出去吧。學生每年前往圖瓦一到兩次。 “我的老師和我參觀聖地,採集藥用植物,他給我新的祈禱和修行。這讓我轉到下一個“學校班級”,我要帶著新的“教科書”回家。從拿到kuzungu(魔鏡)的那一刻起,巫師的修行就變成了接待病人。後來,塔拉斯·鮑里索維奇將薩拉托夫、莫斯科和德國的其他學生帶到了圖瓦。 “小薩滿套裝”裝在普通包包的口袋裡。塔拉斯·鮑里索維奇小心翼翼地展開紅色和橙色的破布,拿出一個帶藍色尾巴的金屬圓圈。說實話,真的不像鏡子。 Kuzungu 由青銅合金製成(較早使用隕石鐵)。一方面,它是光滑的,另一方面,刻有東方十二生肖和符文銘文。 “非常強大的東西。 13-14世紀流傳於蒙古。老師從那裡帶來的。 “然後給了你?”我問。 “我沒有給它,但傳遞了它。他不是主人,塔拉斯皺眉。他有些遺憾地補充道:“總有一天,我也必須把它傳遞給合適的人。”鏡子把痛苦從病人身上引出來。它具有顯示事物本來面目的奇妙特性,無論我們喜歡與否。 Artysh粉(北京杜松)用甜點勺裝在袋子裡。香爐在病人所在的房間裡點燃。任何治療都是從命運的定義開始的。在 41 塊石頭上算命 - huanak(Taras 在 Arzhan 收集了它們)。關於長壽、知識積累、在路上、在法庭上、在閱讀句子時等的祈禱和經文都收集在多色紙板文件夾中。當然,薩滿必須有一套 manchak 套裝。這是一件帶有緞帶、鈴鐺、繡有骷髏頭和陰陽標誌的長袍。塔拉斯的衣服是由一位熟悉的裁縫縫製的。手鼓是由 Taganka 劇院的一位大師製作的(這位老師後來將這些工具神聖化了)。
十年來,Zhurba 有大約 300 名患者。他和很多人成為了朋友。 “薩滿的任務是幫助人們找到與上帝的聯繫。為此,他使用占星術分析、與靈魂的對話和交流,- 塔拉斯·鮑里索維奇 (Taras Borisovich) 說。 - 幫助一個人清除邪靈的有害影響,克服困難的生活處境,找到愛,與親人和諧相處。薩滿還舉行葬禮,沿著白色的道路護送死者。機會多多的魔術師能夢想到什麼?塔拉斯有一個相應的夢想:“努力使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成為一個共同點,呈現一種新的文化語言,讓各種各樣的人都能理解。”薩滿教義是最古老的教義之一,包含許多年輕文化的元素,可以成為這樣一種語言。薩滿教中的至尊神,叫做長青天,父親。它存在於每個生物體內,賦予我們感知周圍世界並賦予其意義的能力。他神聖的妻子是地球,所有生物的母親,這使得實現計劃成為可能。今天,在文化、技術和環境條件下,人們要么照顧他們共同的家園、地球,要么一起死去。在 Zhurba 看來,他會成功 - 薩拉托夫位於連接歐洲和亞洲的地理位置並非毫無意義。首先,塔拉斯·鮑里索維奇 (Taras Borisovich) 製作了一部關於他的老師和薩滿教傳統的紀錄片《白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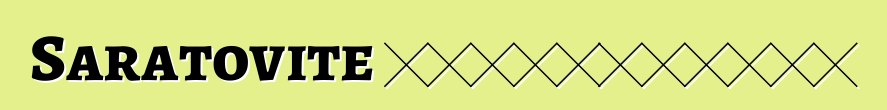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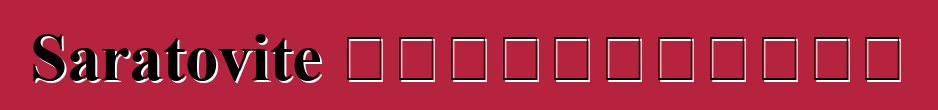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9:50:53 +0300 GMT
0.009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