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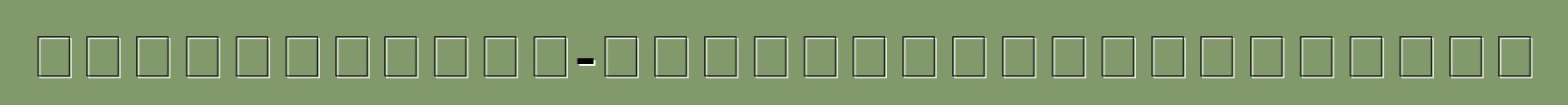



俄罗斯联邦萨拉托夫联邦安全局局长
潘科夫 N.I. 上校
来自萨满宗教团体的主席
库尊古-埃伦
茹尔巴·塔拉斯·鲍里索维奇
打开信封。
今天,2010 年 1 月 20 日。 13:00 我是图瓦“Kuzungu-Eeren”萨满宗教团体伏尔加分会主席 Zhurba T.B. ,哲学科学候选人,绝食。这次绝食是对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特别是其萨拉托夫部门负责人 N.I. Pankov 上校的行动的一种民间抗议形式。它将在与恢复俄罗斯联邦平民的权利有关的条件得到满足后终止。
公民抗议的原因是自苏联时代以来俄罗斯仍然存在的对信仰的迫害、对“异议”的破坏和镇压、对良心自由的歧视的做法。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努力解决众所周知的侵犯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公民公民权利的事实。我试图在我想与 FSB 合作实施的团牧师国家计划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并将其视为俄罗斯联邦公共安全新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有问题的恶毒做法是通过 FSB 可以使用的特殊方法进行的,它影响了俄罗斯联邦的人民,滥用了它的权力。她使用的心理折磨方法,用于令人反感的,以及其他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不会导致她的管理水平提高,是无心残忍和变态的表现渴望给手无寸铁的人带来痛苦。我认为这一传统是过去的遗留物,是俄罗斯发展基于公民和解与和谐的社会的严重障碍。
FSB 侵犯了公民的良心自由、住宅不可侵犯性的宪法权利,干扰了工作和休息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对于不受欢迎的人,其中也有许多该组织的成员,使用全世界禁止的方法作为心理折磨。
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内容。通常,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滴水声、鼓声或其他节奏结构明显的高速音乐在夜间、白天-邻居的修理声,以及其他干扰正常活动的噪音意识和潜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听觉的门槛和注意力的边缘,有时 - 相反,震耳欲聋,与日常噪音混合,并且在场,就像在一个人的自然环境中,或者在他睡着了,这些声音并没有被个体的意识所感知,同时对他的潜意识有着毁灭性的影响。在非常易受影响和天真的人的情况下,这些可以是员工的声音,他们会代表“天使或恶魔”评论他生活中的私密细节,用老练的诽谤代替一个人的良知和常识。
由于影响 - 违反大脑活动机制,心力衰竭,慢性疲劳综合症,抑郁症,生活意义丧失综合症,心理和思想创伤。这些也是各种身体健康障碍,首先是尾骨疼痛和沉重,然后是头痛、慢性神经衰竭、神经症和精神病。这种疾病会以不合理的丰满、有时消瘦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导致慢性疾病、距离、瘫痪、中风、心脏病发作、蛛网膜炎、生殖器瘘管和许多其他疾病。通常,这种方法伴随着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令人反感的公民的中毒。一旦业主离开公寓,他们的食物中就会添加毒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是传染病的菌株,从严重的流感和扁桃体炎到葡萄球菌和链球菌。随着它们的不断使用,急性中毒会导致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此外,这些药物会破坏牙齿,在进餐时去除牙齿中的钙,破坏生殖器官和消化器官活动的药物。神经紊乱可因麻醉物质而加重。它们可以添加到食品、肥皂、护手霜、吸入剂和除臭剂中,伪装成传统品牌的传统香水。精神兴奋剂会加剧屋内声音引起的歇斯底里反应,首先会引起攻击性和暴怒,这是一种多动症 - 未来会导致精神崩溃和神经衰弱,黑色忧郁。
户外观察员的压力可以补充心理影响,他们到处都挑衅地陪伴着他,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带有黑色窗户和数字“666”的黑色汽车戏剧性地追赶,这可以用前灯使他失明,在入口处与他相遇晚上等
一个人一旦处于这样的位置,就会受到白乌鸦角色的威胁。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他决定谈论这件事,这将导致这个人精神错乱的想法。这就是这种做法的目的。当人们以自己的正确性向亲人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如有必要,在神经病学或神经外科诊所住院期间可以实现特定的精神错乱,即使在普通部门,当“他们的”医生开出治疗方案时,也会对患者或精神病院产生非常可悲的结果,他的大脑将永远被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摧毁。
通过关闭手机加强对不需要的人的封锁,当钱每次到达那里时都会从帐户中提取,使其无法使用。互联网页面也被破坏,从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诋毁他和他的收件人的令人厌恶的消息,计算机被植入那里的病毒禁用,计算机系统崩溃,等等。陷入这种“发展”的人的生活中最可悲的是,当与他们一起进入的人受到同样的影响措施时,他们周围就会建立一定的“焦土”领土在家里或工作中联系。这意味着,这个人的所有亲信,都被特勤机关为所欲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无法无天的人质所挟持。他的选择将是这样的 - 至少与某人沟通,假设他可以期待这些人,或者不,在他的家乡仍然是一个完全被抛弃的人。
这种影响的总体策略符合“有罪推定”计划,迫使人们从头开始找借口,失去主动性,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变得脆弱并准备抓住任何解脱的机会,一份慷慨的施舍这条狗被主人接受了自己独裁者的观点,成为他顺从的欲望执行者。内疚的情结,奴隶的地位是这种影响得以实施的背景。它是在 NLP 技术的帮助下进行的,并且符合某些心理方案。他们会强迫一个人夸大可怕的克格勃所带来的危险并违背他们的意愿行事,采取不正当的立场,损害他们的良心,诽谤自己,在家庭心理恐怖的影响下有意识地投降或无意识地按照诱发的心理行动将一个人带到那里的计划,在那里,木偶操纵者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员工。
整整几代人都以道德堕落和堕落的态度发展,解决这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日常和意识形态问题。家庭破裂、自杀、语义迷失、虚假的世界情感图景、绝望的崇拜。这也是醉酒和毒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生存意味着酒精和药物的医疗使用,这成为一种生命支持系统,拐杖,没有它一个人就无法生活和工作。
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俄罗斯的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有思想”的人,能够在生活中占据独立的位置。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在我们国家中不需要有独立人民的安装。除了知识分子,受害者和继续受到影响的人中宗教、科学、艺术的最佳代表是特殊服务的雇员本身。其中,毁容下属的家属,以谋取他们的忠诚,往往是常态。我知道有几起这种影响对公民和情报官员造成致命后果的案例。长期以来,民族的头脑和心脏已经被摧毁和残缺。我们的大脑作为“comprachos 的受害者”进化了很长时间,被放置在一个只有丑陋的侏儒才能生长的容器中。
FSB 不是俄罗斯建国的化身象征。此外,她公开否认这些事实,以一切可能的愤世嫉俗的态度要求提供这种影响的证据,羞涩地躲在她虐待狂的幕后,然后等待夜幕降临,使妇女、老人和儿童生病。同时声称自己与此事无关,不敢公开表态。这种做法为世界上许多特殊服务所熟知,(我还曾治疗过在国外、德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俄罗斯公民,对他们来说,这种做法被用作对付克格勃特工的预防措施,如果被发现,将被阻止)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海牙人权公约谴责为危害人类罪。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明显的残忍之外,它在适用的情况下就其法律和道德有效性而言还意味着绝对荒谬。窃听制裁由检察官发布,但是,除了 FSB 结构本身之外,应用程序的权宜之计不受检查和控制,并且这种活动,酷刑,未经任何人授权,原则上是非法的,即,它是在个人员工一时兴起处置官方“地狱机器”的完全任意性下进行的。
在这些事实中存在着“反人类罪”,这意味着对自然权宜和道德正确性的意义和逻辑的完全歪曲,在这里被颠倒和玷污,以至于人性的理念可以被玷污了。如果 FSB 需要证据,则可以收集这些证据并将其作为公民的一系列观察和证词来证实这些事实。当然,你可以是墙后不断哭泣的孩子的受害者(实际上,孩子不会那样哭很长时间,此外,如果你仔细听,他们不会这样做,重复某些场景像录音机一样哭泣,在他彻底崩溃之后,所有的希望、绝望、孤独和对整个世界的不公平怨恨,无能为力)注意哭泣的人为本性,以及哭泣的事实邻居实际上并没有婴儿、修理或其他表面上无害和自然地破坏心灵的声音。人为和预谋是识别这些行为的一种方式,除了那些绕过国际和俄罗斯法律而被点名和隐瞒的证据之外,还有许多证词是证据。
我以自己的生活和治疗实践为例了解这些事实。曾经,当我的父亲,现在是当之无愧的退休人员,劳动退伍军人,苏联的发明家,然后是国防研究所的一名年轻雇员,拒绝担任第一部门的线人,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为了“敲打”他认为无可挑剔的专家和爱国者的员工,我们的家庭开始遇到麻烦。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住过大约 20 次医院,有几次我是凭“死亡收据”出院的。在我在历史系学习的 SSU,我在党委里被僵尸化了,因为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是不好的,想想他们的内容,他们是为了为他们祈祷,而不是阅读。在保证不离开的情况下,他们给了我特别保管处的书,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书,关于真正的宗教意识是什么。有室外监控、监听、“夜间音乐”等。然后,当我在圣三一大教堂担任敲钟人时,我开始在亲密的朋友圈子里尝试灵修领域。正如我后来意识到的那样,我被归功于宗派活动。之后,我住进了医院,离开医院后,我在脑血管痉挛引起的疼痛休克中度过了四年。我回到我的床上。
我的家庭就像我父母的家庭一样分崩离析。我继续通过灵修和理解宗教真理的道路寻求康复。在我遇到我的老师,第九天堂的白萨满,Tash-ool Buuevich Kung(08/23/1997,图瓦克孜勒市)的那一天,由于他的大慈悲,我的疾病消失了。我去掉了残障组,开始自己给别人治病。我接受过各种疾病的治疗。萨满祈祷 - tarina - 在不同情况下提供帮助,如有必要,辅以图瓦稀有药用植物。它们还有助于克服“克格勃发生器”引起的疾病。然而,由于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做出额外的努力,这是可能的。我有很多患者受到这种暴露的影响。宗教获得了公开存在的能力,但音乐却在夜间继续响起。我治疗了各种精神道路的从业者,东正教徒、佛教徒、“castanedics”、大学教师、艺术家、音乐家、商人、装载机、工程师、FSB 官员本身、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警卫、退伍军人和家庭成员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 GRU 的成员,以及俄罗斯联邦的行政总统。说到后者,面子控制的手段非常严格,所以相对于自己,他们宁愿不要使用八音盒,以免破坏面子。此外,他们甚至对人脸上的血管进行光疗。众所周知,那些被迫在这些方法的影响下生活的人很难避免服用兴奋剂和每日奠酒的后果,除了制造它们的愿望外,还会在脸上留下痕迹。然而,就抑郁症和我所说的疾病的实际治疗而言,克里姆林宫诊所的潜力似乎不如祈祷有效。这并不奇怪——没有什么比人类的温暖更温暖的了,而人们最容易接近的东西来自上帝的礼物。
2000 年,当我在萨拉托夫注册图瓦萨满 Kuzungu-Eeren 宗教组织的一个分支时,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我的师父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道德正直和不屈不挠的榜样,这是克服这种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杠杆。我向 FSB 提出了一些倡议,可以促进他们在反间谍活动和互动方面的活动,特别是与美国大脑研究所的员工和其他人的互动,同时暗示我的爱国立场,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那里有军事职责的例子和宗教服务是相关的事情。这并没有帮助我从这个组织获得互惠。此外,在这件事上提供帮助的我的佛教朋友们,以及与政治无关的和平、正直的公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肉体毁灭的可能性出现在我和师父面前。不幸的是,与外国间谍虚构的荒谬联系,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张声势 - 我们老师的一名学生是苏格兰场的雇员(感谢上帝,对俄罗斯忠诚和相当尊重) - 以及对祖国的叛国罪 - 结果出来了成为比准备更可靠的盾牌实际上可以帮助她并保护她免受这种侵犯。
我在不言而喻的软禁状态中度过了几年,无法离开家。我的家人和我一起分担这些苦难——直到我妻子觉得女儿的身心健康比证明她不是骆驼更重要。这三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家人一起生活。我的母亲,由于在欺凌期间获得的神经衰弱(现在我们不再在家里给食物下毒,仅限于音乐问候),不吃,不在家里储存或烹饪食物。
在 Chekists 报告的那些消息中(实际上,当您的职业代表受到尊重时通常使用该术语,但毕竟是“fesbeshniks”)通知他们受到影响的病房“地狱机器”他们的计划。当然,这首先是最喜欢的狗吠声,预计会有咳嗽反应或其他反应,表示同意分享他们的命运并毫无疑问地服从他们的“恩人”的命令,无论多么有能力和权宜之计,这些鬼脸是为一个在家的人准备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应,那么他们就会把他当作“就好像他住在美国一样”——陌生人。失败时发出威胁声。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可能是仁慈态度的声音和声音,合作邀请,尤其是男女之间的随意交谈。我不接受与 FSB 的这种形式的恋爱关系,尽管我什至听说过,尽管作为“英国间谍”、大学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多年被洗脑,而不是俄罗斯牧师的正常生活。这是荒谬的高度,意思完全颠倒——爬上别人的婚床,认为这是合法的,代表国家这样做,但同时又不断地公开否认这样的事实,并证明第三个不是多余的,据说国家存在于那里,尽管并且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对你的组织有任何爱,因为它要么代表国家,要么不代表。一个女人不问就闯进房子,取代她真正的妻子,把自己当作她的假人,此外,还有一辆救护车来报复和报复,而且不遵守任何诺言,怎么可能没有爱呢。我知道您的组织还有其他体面的人。我反对 Baba Yaga 在道德家的化妆中残忍恶心的无耻面孔,在一面扭曲的意义残缺的镜子中炫耀,我希望这将使我们国家的人民有机会看到 FSB 的其他形象,而不是这些面具比“他们的俄罗斯”牧师、军事企业的工程师、历史和哲学教师、战士以及所有那些按照宪法命令准备保卫自己的祖国或干脆活下去的人更重视“精心打扮的英国间谍”并为它的利益而努力,正如你所知,家园始于家庭和“住在邻近院子里的忠实同志”。你应该让家人在家里不受侵犯 - 并在公共场所谈论工作或违反法律和秩序,如果你有能力让某人为此定罪的话。否则,我多年来一直听到的吠叫声更像是贵组织的声音,而不是人类的声音。它的功能更多地对应于“狗头”oprichnina,而不是保护人文规范的现代形式。
宗教的方法是治愈你自己,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努力的结果中受益。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与其他人的生命相关时才有意义。如果我们谈论疾病,那么康复就是消除疾病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它的症状。因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向您呼吁,在实现了对我家人权利的保护之后,(我可以更容易地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与 FSB 官员的某种熟人)确保我的老师和我们国家的所有信徒,同样地,所有其他公民都不会患上一种非常重要的疾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把常识翻个底朝天,并保护他们免受无动机的残忍和相互的伤害冷漠,允许彻头彻尾的谎言,伤害无辜的人,并接受人们作为不露面的乡下人。如您所知,我并不反对 FSB,也不反对您个人,相反,我倾向于将您从图瓦转移到萨拉托夫视为一个好兆头。我反对 FSB 对自己的员工和人民使用不人道的方法。反对对真相视而不见。
这并不能免除您对已签署的通知说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责任。正如这并不能免除您的员工对您的行为的责任,他们为您准备了回复,以不同的人代表您说不同的话的方式签名。这表明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FSB 的组织程度仍然意味着不负责任以及由不具备适当能力的人解决特定问题。
最近,俄罗斯社会在改善道德风气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的团牧师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邀请您和您的员工参与由宗教和公共组织拍摄的白龙电影,相信您的能力和能力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新条件下得到更多的使用。当然,您的权利是对此类信息安全问题的研究感兴趣或不感兴趣。我明白这一点,不能强加。
但是,我记得在您以前的服务地图瓦,1944 年有 3.5 名巫师和大约 10,000 名喇嘛被 NKVD 射杀。尽管 NKVD 帽上的矢车菊蓝星作为达赖喇嘛之星的象征出现,他通过它获得了洞察力,但它们是他对俄罗斯军队加持的结果。
我的老师,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幸存下来,今天是图瓦萨满教的最后一位老师。他经历了信仰受迫害的所有岁月。他通过对神职人员的各种形式的镇压幸存下来并忍受了教义。反对这种意义的扭曲,当他们要求你将你的信仰象征作为你的头饰时,作为主要的头饰,然后摧毁它,可能,从而试图取代你的位置。
正是由于他在 1987 年被捕,才通过了一项关于宗教活动合法化的意见——幸运的是,在这些克格勃官员中,有他的病人和朋友,他们确信他显然是正确的。
他建造了两座喇嘛教寺庙。他与尊贵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其他著名的佛教导师保持联系,如喇嘛奥列尼达尔和尊贵的噶玛巴第十七世、南开诺布仁波切,以及俄罗斯的大牧者、敏锐的长老基里尔大主教、谢库曼依安、我们的 Hesychasm 教授 N.I. Petrov 的同胞导师。通过千里眼,这些人没有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就低得多的人,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谎言将不再取代我们国家的真相,真诚的仁慈态度将遭到恶意和血腥的报复。
我将停止绝食抗议,除了看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不再受制于您的方法之外,我的老师将从图瓦 - 从您最后的服务地点通知我,他和他的家人也拥有一切在这方面没问题。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精神教义,没有它一个人就不能认为自己足够人性化,至少有一个公共安全保障的最低点 - 在俄罗斯以真正在家的方式生活在家里。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改变的,不需要证明,阴阳标志的图像,东正教十字架,以及五角星,作为宗教标志,在房子的门上,以及在士兵的集体坟墓上,是俄罗斯国家遵守其基本法的保证 - 宪法,礼貌和尊重邻居的内心世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要导体。
有问题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您真诚的 Zhurba Taras Borisovich。
对于所有阅读这些文字并认为这些事实与他个人或他的亲属有关的公民 - 请联合起来保护你的人面和生存,请致电
8 845 2 56 31 59
要么
89170235287
对我个人而言。目前,正在开设一个公共组织“Clear Light”,它将协助宗教组织以及所有理智的人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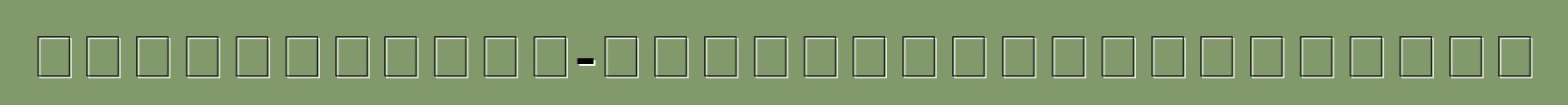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46:49 +0300 GMT
0.002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