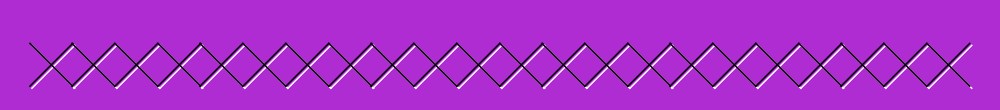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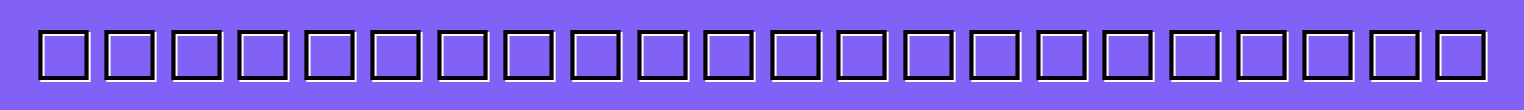




致幻剂和精神药物是世界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我们转向世界的哪个地区,我们都一定会遇到当地药物的使用。墨西哥人民长期以来一直使用致幻的仙人掌 (mezcal) 和 psilobicine 蘑菇,在南美洲他们咀嚼古柯叶,在北部和中部他们吸入烟草烟雾,大洋洲人民酿造了一种令人陶醉的饮料——从胡椒根中提取的卡瓦酒植物,在亚洲,他们食用各种基于大麻和罂粟的药物,在中非 - 从可乐树皮中提取的饮料。此外,致幻剂的消费通常与仪式和仪式实践有关,并且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传统,已为众多书面资料和考古发现所证实。
必须假设在公元前很久以前就在西伯利亚。 e.当地精神药物的醉人特性是众所周知的——大麻、天仙子、野迷迭香、猪草和其他自古以来就在欧亚大陆用于制备麻醉药品的植物。一个已经成为教科书的例子 - “Scythian bath” - 希罗多德描述的黑海斯基泰人集体吸入大麻烟雾的方法,恰好在西伯利亚找到了考古证据。在 5 世纪挖掘 Pazyryk 土墩期间,在 Gorny Altai 的领土上。公元前。在永久冻土的镜头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斯基泰麻醉剂时期的配件 - 小圆锥形小屋覆盖着毛毡和皮革,其中一个下面有青铜器皿,上面有烧焦的石头和烧焦的大麻种子,一个装有大麻种子的皮袋绑在上面另一个的极点 (Rudenko, 1962)., pp. 242–243)。
大多数情况下,西伯利亚人民的麻醉经历与另一种植物 - 木耳有关。目前,关于在西伯利亚人民的仪式和仪式实践中最广泛使用木耳的奇特科学神话已经形成。它在西方历史学家和民族药理学家中尤为常见(Wasson,1968 年;McKenna,1995 年;Jasm 和 Thorp,1997 年)。此外,食用飞木耳必然与西伯利亚萨满教有关,在世界古代和现代人民的采蘑菇仪式中发现了许多与萨满迷幻药的相似之处。但这真的是这样吗,致幻蘑菇在西伯利亚如此普遍吗?西伯利亚萨满教与飞木耳的精神药性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西伯利亚巫师一般是如何使用药物的?本文试图理解这些问题。
鹅膏菌和鲶鱼:科学神话的诞生。
民族真菌学 [1] 的创始人 Gordon 和 Valentina Wasson 首次注意到麻醉蘑菇(包括飞木耳)在仪式实践中的作用。他们发现了美洲和古代欧亚大陆存在蘑菇崇拜的许多例子,这使他们甚至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为真菌爱好者和真菌恐惧者。在他们的共同工作中,这对夫妇提出了另一个原始假设,根据该假设,著名的吠陀经 soma 是在带有红色帽子和白色斑点的蘑菇的基础上制备的,即来自飞木耳 (Avanita muscaria) [Wosson,沃森,1957]。最后一个想法由 G. Wasson 在他的书“Soma:不朽的神圣蘑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他甚至指出了制作这种饮料的传统的可能起源时间和地点 - III 之交的西伯利亚 -公元前二千年,将它在印度的出现与雅利安人的重新安置联系起来 [Wosson, 1968]。 R. G. Wasson 的假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神话学的主要研究人员对此做出了回应 [Levi-Strauss, 1970; Elizarenkova 和 Toporov,1970]。在批评某些有争议的条款的同时,整个假设被接受,毫无疑问,飞木耳在西伯利亚人民的萨满教实践中被极其积极地使用。 T. Ya. Elizarenkova 和 V. N. Toporov 甚至发展了这个想法,将关于飞木耳的想法与萨满(世界)树的语义联系起来,并找到确认飞木耳和鲶鱼之间联系的变体,G. Wasson 没有注意到 [Elizarenkova , 托波罗夫, 1970]。
民族真菌学的形成和围绕它展开的讨论,除了毫无疑问的富有成果的结果——引起人们对真菌在神话中的作用的关注之外,还产生了几个相互关联的结果,主要是对西伯利亚的研究。首先,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即把木耳当成萨满蘑菇;其次,开始寻找确认西伯利亚古代人口文化中蘑菇仪式的存在;第三,西伯利亚人民对所有麻醉剂和致幻剂的消费开始完全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回想一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苏联不言而喻地禁止药物研究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西伯利亚寻找考古证据。
古代存在蘑菇仪式的想法几乎同时出现在西伯利亚的考古学家 - 原始艺术研究人员中。 1971 年,N. N. Dikov 在楚科奇出版了 Pegtymel 的石刻,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 - 公元一千年,其中一些包含“蘑菇”情节:戴着蘑菇帽和蘑菇状物体的拟人化人物。作者将它们解释为人飞木耳和飞木耳,发现古代特定蘑菇仪式的存在得到证实,主要是与亚洲最东北部人民的麻醉会议的民族志相似 [Dikov, 1971; 1979] (158–159)。
继 N. N. Dikov 之后,M. A. Devlet 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了叶尼塞萨彦峡谷岩画中戴着宽“蘑菇形”帽子的拟人化图像,将它们与西伯利亚的毒蘑菇崇拜联系起来。这些图像的年代也非常广泛 - II - I 公元前一千年。 (达夫莱特,1975 年,1976 年)。尽管没有任何严肃的论据,该假说还是找到了权威的支持者。 A. A. Formozov 提议将这些图像与在亚洲广为人知的令人陶醉的苏摩饮料的生产联系起来(Formozov,1973 年,第 264 - 265 页)。在这个地方,考古学和神话学的研究路线终于结束了。 G.M. 在书中以最详细的方式介绍了两者。 Bongard-Levin 和 E. A. Grantovsky “从斯基泰到印度”。参考 R. G. Wasson 的观点,作者还认为木耳可能是古代印度-伊朗人可以从中制备躯体的植物之一,甚至在印度-伊朗人民的宗教传统中建立了一个关于存在的优雅概念“一系列北方萨满教的基本特征”(Bongard -Levin, Grantovsky, 1983, pp. 119–121)。特别有趣的是,这个由神话研究人员提出的想法从考古学家那里得到了反馈。因此,E. M. Meletinsky 引用了一个关于 Itelmens 中的飞木耳女孩的神话故事,正在 Pegtymel 的岩画中寻找证实(Meletinsky,1988)。
上述研究人员的权威性如此之高,假设的规模和表现力如此之大,而且通过民族志类比证实了作者最广泛的博学,以至于下一代考古学家似乎已经抛弃了所有的疑问。在远东考古学中,倾向于将所有类似于蘑菇的物体解释为木耳,并将它们与致幻植物的崇拜联系起来,参考公认的权威并引用非洲、亚洲和非洲人民对它们的使用最广泛的类比。美国。这就是 M.A. Kiryak 在楚科奇西部考古遗址的石头上看到蘑菇图像的方式(Kiryak,1998 年,第 106-109 页,图 1、2); A. G. Garkovik 在来自滨海边疆区 Evstafiy-4 定居点的粘土物体中 (Garkovik, 1988, pp. 50–54, fig. 1)。这些作品无可争辩的优势是年代相当准确:在第一种情况下,放射性碳测年为公元前 2500 年,在第二种情况下,根据文化层的年代测定,下半叶是公元前 3 千年末。最后的日期是最早的,但作为飞木耳雕像的帽子碎片呈现的粘土物体与原型只有遥远的相似之处。顺便说一句,这同样适用于其余图像。古代艺术研究人员对蘑菇研究的精髓已成为 M. A. Kiryak (Dikova) 书中的一个章节(Kiryak,2000)。在这里,与其他此类作品一样,大量参考了前人,甚至在作者不知道的作品中也经常发现真菌(Okladnikov,1976 年;Okladnikov 和 Zaporizhskaya,1969 年,1972 年;Tivanenko,1990 年);来自V. N. Toporov (Toporov, 1987) 的作品,在他们的解释中不仅不证实考古地块,而且经常与他们相矛盾,R. G. Wasson 的强制性脚注,其质量毫无疑问是从 M. A. Devlet 复制的(相同标题中的错误实际上表明作者没有看过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作者完全缺乏关于早期信仰形式的想法,尽管如此,这些信仰却经常被提及。
在考古学家解释蘑菇形物体的尝试中,新西伯利亚研究员 A.P. Borodovsky 的假设脱颖而出,他找到了一种更合理的方法来解释在铁器时代早期的 Bolsherechenskaya 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五件粘土物品的用途.他认为它们是陶瓷生产中用来平滑容器壁的砧座。与他的同事不同,A.P. Borodovsky 没有引用推测性的观点和遥远的类比来证实这一点,而是引用了实验数据,其结果是非常有形的。尽管正是这些材料的“蘑菇状”性质是最没有疑问的,因为它们确实是蘑菇状的物体:它们有一个凸起或扁平的帽子,在一个带孔的短茎上有悬垂的边缘,在帽子内部有小孔(完全不起作用)。总的来说,正是上述所有项目中的这些项目与飞木耳最相似。顺便说一句,他们发现的情况也最不适合他们的功能解释。五分之四的铁砧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所有这些都在男性墓葬中(Troitskaya, Borodovsky, 1994, pp. 119, 121, 126),尽管在养牛业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社区中的陶器很可能是,应该由女性完成。此外,还发现了一个铁砧以及一个石制香炉、几块粉笔和一面铜镜——一种魔法仪式复合体(Troitskaya,Borodovsky,1994 年,第 121 页)。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后一种情况,古迹发掘的作者 T. N. Troitskaya 以前认为 Bolsherechensk 人的蘑菇形物体是仪式。考虑到 A.P. Borodovsky 的假设,我们不得不说,即使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蘑菇形人物是否是木耳菌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国内岩画师的作品整体上从时间和空间上为亚洲蘑菇崇拜的传播描绘了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如果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在公元前 3 千年末,亚洲东北部就开始使用木耳。而且,这一传统直到民族志现代性才被打断。考虑到萨彦峡谷的发现,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古代致幻木耳的分布区域正在显着扩大,它包括南西伯利亚,并与中亚蘑菇崇拜融合,从中获得了著名的鲶鱼。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人关于木耳的想法可能是从中亚和南亚人那里衍生出来的,并从外部出现在针叶林地区,这种可能性是相等的;反之亦然,他们从北方来到这些地区。这里确实存在重大反对意见。首先,空间在古代是文化交流的严重障碍,此外,在民族志时代,除了亚洲针叶林地区外,任何地方都不知道食用木耳,具有致幻特性的木耳只在某些地区生长,这是现代民族药理学家和远见者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其次,即使你在石像中看到蘑菇,也不一定是木耳。总的来说,所有作品中蘑菇形形象与木耳的联系,都是通过北方民族志类比进行的,又必然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 “在关于西伯利亚和远东人民的民族志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萨满巫师使用飞木耳(或从中提取的饮料)[2] 来达到狂喜状态的信息,其中“第二个愿景”打开(Kiryak,2000),-这是考古学家关于问题本质的典型想法。最有趣但也最脆弱的是飞木耳形象的“萨满”基础。为了澄清这种情况,让我们看看在西伯利亚人民的传统文化中,木耳究竟是什么。
西伯利亚北部人民对鹅膏菌的消费。
食用毒蝇伞 (Amanita muscaria) 的传统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人民中广为人知。 VG Bogoraz 认为,飞木耳令人昏迷和兴奋的特性是由“东北亚原住民”发现的(Bogoraz,1991 年,第 139 页)。 1787 年,东北地理探险队的一名成员在 Itelmens 中观察到它:“......不喜欢木耳,也许,因为缺乏木耳,他们试图喝那些发疯的人的尿液,因此他们比第一个更疯狂“(白天记忆......第170页)。众所周知,食用蝇伞在科里亚克人中尤为普遍;南太平洋的楚科奇人和南部的 Itelmens 群体也使用木耳。然而,在这里,在人种学时代,这些蘑菇的消费也受到以下事实的限制,即并非所有类型的飞木耳都具有精神特性,而且,它们仅生长在针叶林地区,并且可以开采的数量极其有限。但几乎所有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居民都知道这些蘑菇的醉人能力。甚至那些自己不使用木耳的团体也收集它出售给他们的邻居——苔原驯鹿牧民。楚科奇人最常使用干燥形式的木耳。蘑菇是为将来收获的,晒干后每根线串三片。使用时,撕下小块,充分咀嚼,用水吞服。这是科里亚克人的一个普遍习俗,一个女人嚼一个蘑菇,然后把它交给一个男人,让他吞下口香糖 (Bogoraz, 1991, pp. 139–140)。注意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关于发酵,即他们不知道用蘑菇制造饮料,因此与特制索玛的直接联系非常值得怀疑。
显然,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飞木耳的麻醉特性不仅为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人民所熟知。有证据表明,它们曾被雅库特人、尤卡吉尔人和鄂毕乌格里人使用。此外,在西西伯利亚,木耳生吃或喝干蘑菇汤。 I. G. Georgi 对这种药物在汉特人中的消费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人一时食一新鲜木耳,或一饮酒,三取一饮,晒干,受此之后,先是多谈,后自下而上,切得歌唱、跳跃、惊呼。 ,创作爱情,狩猎和英雄歌曲,表现出非凡的力量等等,但之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在这种状态下度过 12 到 16 个小时,最后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用力很大,像个钉了钉子的人,但喝醉了,脑子里就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喝醉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Georgi,第一部分,第 72 页)。上面的引文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摄入生物碱——最常见的植物药物——引起的麻醉状态。
红木耳的成分包括两种生物碱 - 毒蕈碱和肌托品。第一个是最强大的。属于极强毒药。一个人同时摄入 0.005 克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与其他生物碱一样,它只能用作小剂量无毒的兴奋剂。然而,毒蕈碱不会引起致幻作用,假设促肌素(蘑菇阿托品或毒蕈碱)作用于大脑(Astakhova,1977),尽管尚未对人体进行促肌素试验,这只是一个假设。不管怎样,食用含有毒蕈碱的木耳是极其危险的,需要非常准确地计算剂量。
从上面给出的例子来看,西伯利亚人民非常了解“平均”剂量 - 三个蘑菇。但剂量的大小通常取决于身体的一般身体状况、食用持续时间、剂量之间的间隔。年轻人少量使用蘑菇,剂量逐渐增加,剂量间隔缩短,有可能在麻醉梦后以最小剂量立即重复中毒。 V. G. Bogoraz 详细描述了楚科奇人中毒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单独发生,也可以在一次服药期间依次发生。在第一阶段(年轻人的特征),愉快的兴奋开始,无缘无故的喧闹欢乐,灵巧和体力得到发展。第二阶段(多见于老年人)出现幻觉反应,人们听到声音,看到精神,整个周围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呈现出不同的维度,物体看起来过大,但他们仍然意识到自己并正常回应熟悉的日常现象,他们可以有意义地回答问题。第三阶段最难——人进入意识改变状态,与周围的现实完全脱节,处在虚幻的神灵世界中,受神灵控制,但能长期活动,能动能说话, 之后一个沉重的麻醉梦开始了 (Bogoraz, 1991, pp. 140–141)。
但以上所有证词都与萨满教习俗无关;这里我们更多地谈论家庭毒瘾。像所有麻醉药物一样,飞木耳引起典型的中毒;从摄入开始,身体对生物碱产生依赖。飞木耳的习性很强,在没有蘑菇的情况下,情侣们喝自己的尿,或者最近吃过的人的尿,有时甚至是在蘑菇区吃草的鹿的尿。毒蕈碱和 mycoatropine 在体内几乎不被分解,而是以溶解的形式从体内排出,因此尿液几乎与蘑菇本身一样有毒。西伯利亚人民也很清楚这一点。显然,他们关于木耳的特性的知识是食品实验的结果,是根据实际使用经验发展起来的。无论如何,早在 18 世纪,北方人民就已经了解剂量和消费规则。稳定。这本身就表明蘑菇的消费必须经过一定的测试阶段,在此期间制定了食谱和标准。考虑到致幻的木耳菌并非随处生长,而且它们的精神活性会随着每年的气候变化而变化,不得不说这个阶段一定是相当漫长的。即使是堪察加半岛的俄罗斯人,他们从当地人那里借鉴了现成的消费传统,也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 S. P. Krasheninnikov 给出了几个俄罗斯人在这个阶段食用木耳的可悲例子“仆人瓦西里·帕什科夫,经常奉命访问上堪察加和博尔谢列茨基,命令木耳将他的卵压碎,谁在三天内听了他的话,死了。对于和我一起来的翻译 Mikhail Lepekhin,他不知道喝木耳,他命令切开他的肚子……”(Krasheninnikov,1949 年,第 694-695 页)。
自然地,飞木耳会影响心灵,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致幻反应,从而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将消费者带入神圣的境界,木耳自身获得了神奇的力量。在这里,显然应该在消费动机中寻找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从给出的描述来看,这些蘑菇的大量使用绝不是为了神奇的运动,而是一个纯粹平淡无奇的目标。如您所知,吸毒会导致兴奋,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欣快状态。皮质抑制的结果是大脑皮层的活动受到抑制,思维活跃、记忆力、情境情绪受到抑制,但同时积极情绪(喜悦)中枢的兴奋性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瘾君子有吸引力的是后者。因此,我们必须指出,西伯利亚北部人民对木耳的大量消费存在于仪式和礼仪实践之外,最多与它平行。
神话和仪式中的鹅膏菌。
木耳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种现象,自然而然地在食用它的人们的神话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古代意识的麻醉幻觉与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真实,并且无疑需要命名和解释。因此,在楚科奇人中,蘑菇被拟人化为一种精神 - 一种飞木耳,它像真正的蘑菇一样呈现 - 没有脖子,没有腿,有圆柱形的身体和大头,尽管它可以出现多种多样形式。他移动,快速旋转。根据楚科奇人的说法,飞木耳的灵魂非常强大,它们会穿过石头和树木生长,撕裂和粉碎它们。他们与下界有联系,无论如何,他们经常带领他们的仰慕者到死者居住的国家[T。 Ya. Elizarenkovka 和 V. N. Toporov 认为,通过飞木耳的恍惚状态可以与上层世界联系],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危险和阴险,他们需要一个人不断尊重自己和周围的自然,他们迫使他们执行他们所有的命令,不服从就以死相威胁,他们经常开恶作剧,以虚假的形式展示一些东西。 (Bogoraz,1991 年,第 140-141 页;他,1939 年,第 5 页)。 Ob Ugrians 还认为飞木耳中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根据 M.V. Shatilov 的说法:“双关语”(飞木耳 - A.Sh.)......当一个人知道从他那里偷东西,谁欺骗他等的一切时,就会告诉他一个特殊的状态。”
使用飞木耳,人们很容易接触到它们,获得它们的一些神秘力量,有时它们甚至可以自己变成(感觉)蘑菇。显然,只有某些人,最有可能是生理上易感的人,服用木耳的持续动机之一恰恰是渴望与精神世界接触,获得自然元素精神赋予的新神秘机会。这种现象在西西伯利亚很普遍。在汉特人中,飞木耳被英雄故事的表演者食用。 “......这位歌手为了获得更大的灵感,在唱歌前吃了几个飞木耳 - 7-14-21,即七的倍数 [3]:他只是因为它们而变得疯狂,看起来像个恶魔。然后整晚他都用狂野的声音唱着史诗,甚至很久以前,似乎都被遗忘了,早上他精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上”(帕特卡诺夫,1891 年,第 5 页)。正是这种个人经历构成了有关飞木耳萨满教本质的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西伯利亚萨满巫师中,有不少“空想家”在吃完蘑菇后服用木耳或在麻醉梦中拜访灵魂,从而进入恍惚状态。在满西族民间传说中,萨满被称为“食蝇”人。曼西人的英雄故事之一讲述了:“Ekva-Pyryshch 去了,带来了萨满。他在火上挂了一个装有木耳的大锅。巫师开始算命,有木耳,他打手鼓,他算命。 Ekva-Pyryshcha 即将发现这些技巧”(Chernetsov,1935 年,第 77 页)。 K. F. Karjalainen 引用了 Khanty 中的几个此类案例,男女巫师最常使用木耳来拜访至尊天神 Sanka (Karjalainen, p. 306–307)。在汉特人中,在那些知道如何与精神世界接触的人中,有一个单独的木耳菌类别,“吃木耳菌并在半昏迷状态下与精神交流的人”(Kulemzin, Lukina, 1992 , 第 120 页)。一些涅涅茨萨满巫师也服用木耳,以便从麻醉恍惚中的灵魂中找出如何治愈病人(Lehtisalo,p.164)。正是基于这些以及来自西西伯利亚的类似例子,萨满教与食用飞木耳之间联系的假设才得以建立。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木耳使用模式:在东北 - 亵渎,几乎所有社区成员都可以尝试木耳;在西西伯利亚 - 神圣的地方,飞木耳仅供个人食用并严格按照仪式食用。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也不完全是萨满教的做法。人们认为,通过使用药物来达到萨满狂喜的陶醉并不是萨满教的特征。 Mircea Eliade 称这种方法为“粗糙和被动的”(Eliade,p.175)。麻醉恍惚是相当前萨满的,或神奇的。
在西西伯利亚西部,飞木耳的特性更常用于与精神接触,但用于真正的医疗实践。 V. N. Kulemzin (Kulemzin, Lukina, 1992, p. 118 - 120) 充分详细地描述了 Khanty isylta-ku(魔术师和治疗师)使用飞木耳的治疗过程。整个过程归结为让病人入睡,长时间的睡眠和醒来。为了让病人沉浸在睡眠中,isylta-ku 准备了一种相当复杂的药物。他用温水在两个容器中浸泡木耳的干膜和没有膜的蘑菇本身,而水必须是雪的,杯子是木制的,因为在任何仪式实践中,违反既定秩序在这里是不可接受的。服药后,患者应在冷室中睡三天。治疗师自己也带了木耳,他必须和客户一起去地下神 Kali-Torum 交出礼物,并请他不要带走病人。在后者中,由于服用药物,血压下降,呼吸减慢,即发生非常严重的中毒,如果不小心或过量服用药物,可能会发生呼吸中枢麻痹和呼吸停止。 isylta-ku的剂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必须保持清醒,观察熟睡中的人的状态,及时将他从这种状态中唤醒。 Khanty isylta-ku 的医疗实践在语义上与 Carlos Castaneda (Castaneda, 1995) 描述的墨西哥魔术师唐璜使用麻醉仙人掌的行为极为相似。这里排除了直接联系;相反,我们可以讨论古代文化中麻醉药品认知的普遍解释模型。麻醉剂和致幻剂的类似概念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最多样化的人群中广泛传播。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萨满教基础;从本质上讲,飞木耳只不过是一种魔法元素。
另一方面,萨满教属于关于神圣世界的思想更发达的阶段。在他的邪教实践中,始终是人间与灵界之间的中介形象,他是被神选中的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不再只是一个人。但即使对他来说,精神世界也只有在仪式上才能进入,那时他会进入一种特殊的意识改变状态——一种受控的恍惚状态。同时,真正的萨满入神术是不用药物,而是借助于歌唱、音乐、肢体动作、生物体质和长期训练来达到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大多数萨满仪式中,只有萨满本人进入恍惚状态;通常在场的人即使不是被动的观众,也至少不会安排舞蹈表演,就像人们在分析岩画时所想象的那样。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所有民族都没有发展萨满教。在东北民族中,国内盛行萨满教,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萨满教,在鄂毕乌戈尔人中正处于形成阶段,吸收了梦师、魔术师、占卜师、占卜师和说书人的各种法术。并非没有,在这些文化中,精神世界是非常有形的,即使不是每个人,许多人也有可能与之接触。所描述的 18 至 19 世纪的民族正处于改变两种催眠系统(魔法和萨满)的阶段。
恍惚的魔法技术,其中麻醉剂是一种变体,似乎先于萨满教方法。神奇的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与吸毒有关的仪式。萨满教通过音乐、歌唱和肢体动作进入意识改变状态的方法,是萨满教发展形式的特征,出现得晚得多,并逐渐取代了仪式中的麻醉恍惚。显然,与此相伴的是,与灵界的集体接触让位于调解人的个人接触,调解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然地,在这种情况下,吸毒可以作为遗物保留在萨满教仪式中。
萨满教实践中的致幻剂。
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地区,木耳似乎是唯一广为人知的药物,这可能是由于植物资源有限。在植物群更加多样化和丰富的地区,含有精神药物和致幻物质的植物范围更广,草药的使用频率更高。远东人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麻醉品。在民间医药中,作为麻醉剂,有人参根、甜猪草、野迷迭香叶、杜松枝等成分。与飞木耳相比,这些是相当弱的药物,不会引起严重的中毒或致幻反应。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使用需要仔细的,通常是药理学复杂的准备或几种成分的组合。远东人民使用麻醉药品的方式更为多样:麻醉植物被喝醉、咀嚼、焚烧和吸食。
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使用也与萨满教习俗有关。因此,Nivkh 萨满必须在仪式之前和期间练习燃烧迷迭香(ledum palustrel、ledum hypoleucum)。一个特殊的吸烟者是萨满的不变属性,还有一条腰带、一套西装和一个手鼓 (Otina, 1994, p. 102)。 Udege、Ulchi、Nanai 和 Orochi 的巫师也在仪式中使用野生迷迭香。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干树叶扔进壁炉或热煎锅中(Brekhman,Sem,1970,第 18 页:Podmaskin,1998,第 57 页)。烟雾影响了萨满本人的心理,在封闭的房间里创造了一个与灵魂交流的有利环境,促成了在场人员的集体催眠和萨满恍惚。
在阿伊努人中,云杉、落叶松、野蒜和当地名称为 nutya 的植物的枝条在仪式前被放入热灰中。后者是一种弱草药。阴燃着,这些植物散发着芬芳的气味,那烟雾显然是一种微弱的镇定剂。在仪式之前,萨满喝了咸海水,海水中浸泡了云杉和繁缕的枝条。植物的麻醉汁帮助萨满达到了意识改变的状态。在会议期间,萨满又喝了这种液体两三次,不断保持身体的麻醉陶醉 (Spevakovsky, 1988, p. 168)。
显然,在仪式的背景下包含精神药物和致幻药物是远东人民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与精神世界的麻醉恍惚和致幻接触似乎是这些植物营养用途的基础。但是在远东也没有发达的萨满教,而是记录了它的早期形式。
在进入恍惚状态的魔法和萨满的连续变化中,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个趋势:药物越强,萨满恍惚本身所起的作用越小;药物越弱,受控催眠技术就越重要。在极端情况下,后者具有象征意义,几乎不使用直接效果。如果我们考虑在医疗和仪式实践中使用含有极少量麻醉物质的植物,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一种这样的植物是杜松 (Juniperus L.)。它曾经被西伯利亚的许多人使用,现在仍在使用,而且非常单调。杜松烟被熏蒸。燃烧的植物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对人有放松和镇静的作用,西伯利亚的许多人认为这种香气可以净化心灵,对邪灵有害。因此,例如,在治疗患有精神病的 Nivkhs 时,他们会用杜松树枝上的烟雾熏蒸 (Otina, 1994, p. 98)。同时,烟雾的作用被解释为不是麻醉(魔法),而是神圣(象征)。拥有植物的并不是神灵,而是植物,通过烟雾,以自身的自然力量影响神灵,将他们驱离病人。
用杜松烟熏熏在西伯利亚南部尤为常见。在图瓦,杜松 (artysh) 是仪式和仪式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治疗都从熏蒸仪式开始——驱除邪灵。一般来说,凡是可能有恶势力的地方,都要进行熏蒸。这在葬礼和追悼仪式中尤为突出。所以,葬礼结束后,蒙古包必然要熏蒸,在与死者灵魂的亲属追思会上,巫师总是用杜松(san)点燃香炉(Dyakonova, 1975, p. 49, 60)。在专门分析图瓦萨满教必需品的著作中,通常会非常注意服装、手鼓、镜子和精神形象,通常对 artysh 没有任何意义。 (Kenin-Lopsan, 1987, pp. 43–77)。然而,带有干杜松树枝粉末或干树枝本身的灯是图瓦巫师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不止一次看到杜松在图瓦萨满巫师的实践中的使用。萨满会议通常从用 artysh 熏蒸开始。萨满祭司点亮一盏灯或点燃一根树枝,首先净化他自己和他的工具。他通常按照一定的顺序在阳光下将灯围绕物体转 3 到 9 圈:首先是木槌,然后是头饰,立即戴在他的头上,然后是手鼓,最后,他清洗自己将双脚放在闷烧的 artysh 上 - 用左脚三次,然后用右脚,再用左脚两次。在仪式之前,还通过在太阳下在脸上画圈并将双手交叉放在面前来清洁客户。如果举行大型仪式,所有在场的人都会以类似的方式用圣烟净化。同时,在仪式期间,杜松必须不断闷烧,以免熄灭,无论是萨满本人还是从现有手表中选择的助手。高级图瓦萨满 Sailyk-ool Kanchiyr-ool 告诉我一个奇怪的细节。 Artysh 只能在室内持续燃烧,没有必要在户外燃烧。显然,早期的杜松烟更多地用于与精神世界接触。我不得不多次进入熏制杜松的房间,体验它的醉人效果。在这样的房间里呆久了,萨满仪式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这种烟雾的麻醉效果会非常强烈。现在萨满巫师使用杜松而不考虑它的麻醉特性,对他们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自然力量,而不是具体图像中的人格化。在图瓦萨满巫师看来,artysh 有助于与精神接触,以及诸如心、光、声、纯度等抽象的非个性化概念。
西伯利亚南部的其他民族对弱麻醉药的看法也有类似的基础。哈卡斯人还在任何治疗前进行熏蒸仪式,并认为杜松 (Archyn) 的烟雾具有净化作用。尽管用 Bogorodsk 草 (irben) (Thymus vulgaris) 进行熏蒸在其中更为普遍,但其麻醉效果与所描述的相似。给病人熏蒸时,治疗师会说:“用须弥山的Bogorodsk草药熏洗,/使人的邪恶力量得到净化!/让魔鬼回到他们的世界!” (Butanaev, 1998, p. 240)。
图瓦和哈卡斯的巫师使用弱准备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了解强大的准备。相反,是西伯利亚南部的人民知道合成的,因此非常强大的精神药物和致幻药物。合成药物极其危险。除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药物成瘾的快速发作外,它们还最容易引起戒断综合症,即拒绝服用伴随着精神功能的侵犯。即使是相对较短的休息也会导致行为改变、兴奋性增加、易怒和攻击性。那是典型的毒瘾。我们主要谈论通过升华牛奶或谷物发酵产物获得的烈性酒精饮料。图维尼亚人和阿尔泰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准备牛奶伏特加 - araka。哈卡斯人知道两种烈性酒——“airan aragazi”——牛奶伏特加和“as aragazi”——黑麦伏特加 (Butanaev, 1998, pp. 143–149)。显然,在西伯利亚南部开始生产这些饮料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并且与经济生产形式的形成有关。 V. Ya. Butanaev 认为,在吉尔吉斯汗国时期,哈卡斯的祖先就知道以谷物为基础的令人陶醉的饮料,它们在中国的书面资料中有所提及 (Butanaev, 1998, p. 149)。
牛奶伏特加是南西伯利亚所有养牛民族都熟知的饮品,也有着相当悠久的消费历史。早在中世纪,石雕腰带上就描绘了一个皮革烧瓶,类似于阿尔泰人、哈卡斯人和图瓦人的荒木烧瓶。 araki 的制造技术、存储传统和使用在突厥-蒙古世界的所有群体中都非常相似,并且在专业文献中有相当全面的描述。
牛奶伏特加被解释为一种象征价值。它的使用不是魔法行为,它不提供与精神世界的直接联系。然而,它的语义负载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世界上养牛者所重视的乳制品的所有特性。 araki 的使用与一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时刻有关,他们在孩子出生、婚礼、葬礼、会见客人等时饮用它。事实上,这种合成药物的消费伴随着任何庆祝状态,当日常生活退居幕后,社会框架扩大到普遍规模,使人们更接近自然精神的原始世界。阿拉卡和人类一样受到精灵的喜爱,但它不是他们世界的价值,不像魔法阶段使用的强烈植物迷幻剂,它不认同精灵本身。灵魂接受她作为祭品,被她吃掉并被她净化,就像人一样,他们与她一起度过一个假期,对人们怀有感激之情并象征性地接近他们。在这种超越日常生活框架的相互状态中,两个世界——人类和神圣——之间被遗忘已久的神奇接触方式得以体现。这些恰恰是药物古老神奇功能的后遗症,它确保了它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
因此,致幻剂和精神药物在西伯利亚人民的邪教实践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很可能对应于它们使用的某些历史阶段,可以重建如下:
第 1 阶段 - 测试 - 指的是人类探索西伯利亚的最早阶段,当时许多植物只是在食物实验中被品尝过。
第 2 阶段 - 魔法使用 - 意识到药物的致幻作用,人们开始在魔法中使用它们,很可能是集体仪式。从未跨过这一阶段界限的“蘑菇”考古器物和西伯利亚东北部人民对飞木耳的使用可能属于这一时代。
阶段 3 - 遗物使用,当精神药物的力量仅由某些人在仪式和礼仪过程中使用时,最常见的是医疗实践。正是在这个阶段,远东的人民,鄂温克人和鄂毕乌戈尔人,都位于此地。
第四阶段——象征性使用。这是真正的萨满教阶段,当麻醉药品仅被视为符号时,它们在功能上被迫脱离仪式实践进入家庭消费领域,在那里它们成为节日(改变的)社会状态的一个属性。必须假设这些阶段发生在古代,或者仍在进行,所有药物都为传统文化所熟知[4]。
又是鹅膏菌。
基于上述假设,西伯利亚人民认为飞木耳是强大的精神,他们与下层世界的联系以及与他们接触并通过他们与一般精神世界接触的可能性,通过吃蘑菇,是很可能是纯粹的原型,在远古时期由于食物或药理测试、巫术实践的发展以及前萨满教级别的仪式和仪式活动过程中的幻想实验而形成。然后,我们只能在魔法仪式的背景下谈论考古发现中的蘑菇形象(当然,如果它们是蘑菇的话),顺便说一下,集体接受致幻剂和联合舞蹈是可能的,这是许多人想要的在岩石雕刻中看到。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将食用木耳的仪式传统与臭名昭著的索玛严肃地联系起来(我个人非常怀疑),那肯定不能通过萨满教,在萨满教中,药物的使用被指定为象征意义。事实上,仔细观察后,飞木耳蘑菇不是巫术,而是魔法。
文学:
Karjalainen KF Die Religion der Jugra - Volkern。赫尔辛基,1927 年。三、
Lehtisalo T. Entwurf einer Mythologie der Jurak-Samojeden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 - Ougrienne。赫尔辛基,1927 年。 53.
Levi-Strauss C. Levi-Strauss C. Les champignons dans la culture // L`Homme。 1970 年第 10 页,第 5-16 页。
Wasson RG Soma:不朽的神圣蘑菇。 - 海牙,木桐,1968 年。 - 380 页。
Wasson RG,Wasson 蘑菇、俄罗斯和历史副总裁。 — 纽约,Pantheon Books,1957 年。2 v。 — 432 页
Astakhova V. G. 有毒植物之谜。 M.:木材工业,1977 年。第 1 部分。有毒植物。
Bogoraz VG 楚科奇人的物质文化。 M.:科学。 1991. - 224 页
Bogoraz-Tan V. G. Chukchi。第二部分。宗教。 L .: 北海航线负责人出版社。 1939. - 208 页
Bongard-Levin G.M., Grantovsky E.A. 从斯基泰到印度。 M.:思想。 1983. - 206 页
Brekhman II, Sem Yu. A. 西伯利亚和远东人民的某些精神活性药物的民族药理学研究//远东药物。哈巴罗夫斯克,1970 年。问题。 10,第 16-19 页。
Butanaev V. Ya. 哈卡斯民族文化。阿巴坎:哈卡斯出版社。状态大学1998. - 352 页
Garkovik A.V. 小塑料制品反映了古代社会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远东的古代图像世界。太平洋考古学。第 10 期。符拉迪沃斯托克:FEGU 出版社。 1998. S. 49 -58。米。 1;5。
Georgi I. G. 描述了居住在俄罗斯国家的所有民族,他们的日常仪式、习俗、服饰、住所、锻炼、娱乐、宗教和其他纪念物。圣彼得堡,1799 年。第 1-4 部分。
James P., Thorp N. 古代发明。明斯克:花香。 1997. - 768 页
Dikov N. N. 东北亚古代文化。古代亚洲与美洲的交界处。 M.:科学。 1979. - 352 页
Dikov N. N. 古代楚科奇的岩石之谜。 Pegtymel 的岩画。莫斯科:瑙卡出版社,1971 年。
测量员 F. Elistratov 的白天纪念馆,从沿着 Penzhina 湾海岸的 Tagal 堡垒到河流。 1787 年 9 月 14 日至 21 日,在名义顾问 Bazhenov 的指挥下的 Penzhins // 1785 年至 1795 年东北地理考察的民族志材料。马加丹:马加丹书。出版社,1978 年。
Devlet M.A. 来自叶尼塞萨彦峡谷的古代拟人图像 // 西伯利亚古代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之间的相关性。新西伯利亚:Nauka,1975 年,第 238–248 页。
Devlet M. A. Dancing little men // Priroda,1976 年。第 9 期,第 115-123 页。
Elizarenkova T. Ya., Toporov VN 关于蘑菇的神话思想与 soma 的原始性质的假设有关 // IV 暑期学校关于二级建模系统的摘要。塔尔图,1970 年,第 40-46 页。
Kiryak M.A. 西楚科奇旧石器时代晚期图形(移动艺术纪念碑)情节中的蘑菇//远东古代图像的世界。太平洋考古学。第 10 期。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国立大学出版社,1998. S. 106 - 122。
Kiryak (Dikova) 文学硕士远东北部的古代艺术(石器时代)。马加丹:SVKNII FEB RAN,2000 年。- 288 页。
Krasheninnikov S.P. 对堪察加半岛的描述。 M., L.:Glavsevmorput 出版社,1949 年。
Kulemzin VN, Lukina NV 认识汉特人。新西伯利亚:Nauka,1992 年。- 136 页。
Makkena T.众神的食物。 M.:超个人研究所出版社。 1995. - 379 页
Meletinsky E. M. 古亚洲人的神话//世界人民的神话。 M., 1988. T. II.第 274-278 页。
Okladnikov A.P. 下安加拉(从 Serovo 到 Bratsk)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西伯利亚:Nauka,1976 年。- 327 页。
Okladnikov A.P., Zaporozhskaya V.D. Transbaikalia 的岩画。 L.: Nauka, 1969. 第一部分。 — 217 页
Okladnikov A.P., Zaporozhskaya V.D. Lena 中部的岩画。 L.: Nauka, 1972. - 271 p.
Patkanov S. 根据 Ostyak 史诗和英雄传说的 Ostyak 英雄类型。 SPB,1891 年。
Podmaskin VV Udege 对药用植物和动物的使用 // 东亚和东南亚的生物资源及其使用。海参崴:Nauka,1978 年,第 54-60 页。
Spevakovsky A. B. 阿伊努人的精灵、狼人、恶魔和神灵(传统阿伊努社会的宗教观点)。 M.: Nauka, 1988. - 205 p.
Tivanenko A. V. 布里亚特古代岩石艺术。新西伯利亚:Nauka,1990 年。- 206 页。
Toporov V.N. 蘑菇 // 世界人民的神话。 M., 1987. T. I. C. 335–336。
Troitskaya T. P., Borodovsky A. P. 鄂毕森林草原地区的 Bolsherechenskaya 文化。新西伯利亚:Nauka,1994 年。-184 页。
Formozov A. A. 关于苏联石刻的新书(1968-1972 年出版物回顾)// SA,1973 年。第 3 期
Chernetsov V. N. Vogul 的故事。满西族民俗文集。 L., 1935.
Shatilov M.V. Narymsky 地区的 Ostyako-Samoyeds 和 Tunguses // 托木斯克当地传说博物馆的论文集。托木斯克,1927 年。T.I.
Eliade M. 萨满教:迷魂药的古老技巧。 M.: Sofia, 1998. - 384 p.
注意事项:
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中使用蘑菇的科学
不一致 pl。和单位这些数字是引用作者的错误。
这里可能有点夸张,超过七个蘑菇的剂量是剧毒的,可以致命。
回想一下,现代吸毒成瘾与使用传统文化的精神药物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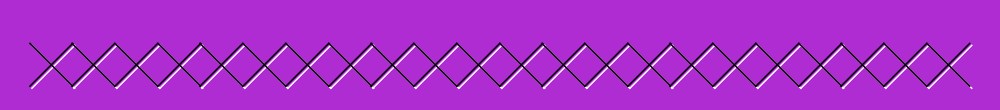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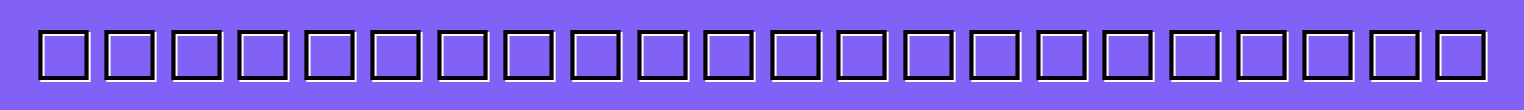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53:02 +0300 GMT
0.010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