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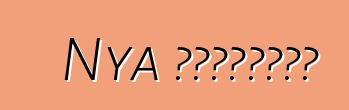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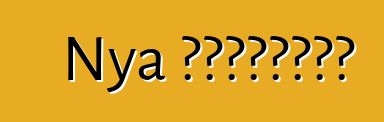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偶然的。在杜金卡市的建筑群中,仿佛是电影《潜行者》的取景地一般,隐藏着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上面写着“地方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我们相遇了,只是一开始我不明白这个有着东方风格的扁平脸庞的粗壮矮个子男人来这里做什么。他站在博物馆最大的大厅中央,一个写着“萨满属性”的陈列柜前,一边摇摇晃晃一边小声哼着什么。几人围在他身边,议论纷纷,男子却没有理会。他完全沉浸在自我中,斜眼几乎一直都在闭着。
显然,这是一种恍惚。然后我很惊讶地看到博物馆工作人员如何恭敬地从储藏室里为他取来一些物品,当他要一套西装时,他们打开陈列柜,让他拿到存放在那里的全套萨满法衣。
对于我的问题,博物馆馆长回答说:“每年一次,他会穿着他父亲的服装来谈话。”我从她那里得知,这是泰米尔最后一位萨满萨满 Lenya Kosterkin,是强大萨满家族 Ngamtusuo 的后裔。他轮流住在 Dudinka(他经常几个月无法离开那里),然后住在他的家乡 Ust-Avam 村,该村位于遥远的北部,在 Byrranga 山脉的门槛上,然后在他的狩猎“点”苔原。
他不打算成为巫师,他听到巫师的呼唤,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人。他离父亲还很远,但 Ust-Avam 的居民相信莉娜身上有“力量”,有时他们会向他提出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求治疗感冒、割伤、瘀伤,但有一次他帮助了一个患有某种奇怪疾病的小女孩——他们没有向我解释是哪一种。他被要求参加家庭假期,或者就如何“喂养”家庭偶像征求意见。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的父亲是如何带他去一个狩猎点的,那是在苔原很远的地方,他们乘坐鹿驾的横梁(拖车)到达那里。在所有山峰、森林和水源处,他都看到了神灵的雕像——这些地方的“主人”,它们是由他的父亲,伟大的巫师图比亚库切割并放置在那里的。 Lenya 和他的父亲过着和所有 Nganasan 人一样的生活:他们打猎、捕鱼、放牧鹿,只有他的父亲还治病救人,在苔原寻找失踪者,并安排了“初雪节”。
“人们总是去找我父亲,”莱尼亚回忆道。 - 父亲从不拒绝帮助。有时,在仪式结束后,chuma 会在地板上躺上几个小时(不可能在横梁上进行仪式)然后恢复理智,就好像被遗忘一样。他失去了很多力量。他帮助许多人摆脱疾病,有一次他在苔原发现了一个失踪的人:他做了很长时间的 kamla,然后指出了寻找他的地方。他躺在雪下,冻僵了,但还活着。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如何和父亲吵架的。然后他用斧头砍掉了溪流中一个偶像的头。父亲甚至没有生气,只是奇怪地看着我,让我把一切都处理好。我当时清醒过来,意识到我做了什么。所以那个偶像站在我们面前,头上缠着电工胶带。父亲原谅了我,偶像也原谅了我。很遗憾当时没跟他好好学习。当他要给我他的主要服装时,我拒绝了……然后他把它给了博物馆。
我们乘坐一艘旧船航行到叶尼塞河下游,然后乘坐直升机飞行。 Lenya Kosterkin 和我们在一起。他需要带孩子去城里,他们和亲戚住在村里——孩子们该上学了。
四排营房式建筑位于阿瓦姆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这是Ust-Avam村。它曾经是泰米尔广阔地区发展的前哨站。现在这里的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的设备。 Nganasans 和 Dolgans 占居民的大部分。村庄的北面是 Byrranga 山脉,这是一种边疆。根据 Nganasans 的说法,在山脉之外,死亡之地开始了。在山脉的这一边——无尽的苔原、沼泽、成群的蠓和成堆的生锈设备。今天,只有少数家庭能够在苔原中生存——那些没有失去猎鹿技能的家庭。
Nganasans 不再有家养鹿 - 最后一头在七十年代被灭绝。村里很多人家附近还停着拉着东西的雪橇。但是驯鹿永远不会被套在这些雪橇上。老人为最后的旅程准备了雪橇和他们的传统服装。
1995 年至 1996 年,一群热心的企业家在地方当局的支持下,试图重振恩加纳桑的家养鹿群。我们用直升飞机从雅库特带来了几只动物。鹿一直坚持到冬天,当天气寒冷时,它们一只一只饿死了。第二次,在冬天,当叶尼塞人“崛起”时,他们试图从河的另一边,从涅涅茨人那里追上鹿。在为期两周的旅程中,几乎整个小鹿群都去了“野人” - 一只野鹿。 “之前,我们让我们的鹿穿过野蛮的鹿群,我们的鹿群曾经增加了几十头。一家人从未离开过,”Lenya 说。我问 Ust-Avam 村的年轻人:“你们现在愿意在苔原放牧鹿吗?”通常,他们摇头:“没有。这太辛苦了,现在一个习惯的都没有了。谁愿意在雪地里睡上几个月?但事实证明,有少数人准备回到他们祖先的事业中。 “村里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其中一位告诉我。 - 在冬天,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于是,去年冬天,我和爸爸锁上了房子,住在离村子70公里外的一个狩猎点的梁上。如果我们有鹿,至少有一打,我们就会去漫游了。狩猎会很好 - 我们的观点已经完全耗尽。
曾经拥有一个巨大半岛领土的人们现在在几个小村庄继续他们的历史存在。恩加纳桑人的数量逐年减少,现在只剩下四千人左右。或许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届时最后一位恩加纳桑的鸟魂将飞到拜兰加严酷山脉之外的亡灵之地。
恰巧,来自杜金卡的老艺术家莫特米亚库图尔达金仍然是全民记忆的守护者。 Motemyaku 的记忆保留了 Nganasan 的生活方式——瘟疫、鹿、雪橇、萨满……传统的 Nganasan 生活的图片现在只存在于他的水彩画上。
神秘传统的最后一位传承人是 Lenya Kosterkin,原名 Lantemyaku Ngamtusuo。直到今天,还有关于 Ngamtusuo 部落的萨满 Dukhod 的传说 - Leni 的祖父。都说他能变狼,一眼就杀人。他总能找到迷失在苔原中的人,救治最绝望的病人。杜霍德作为最强的萨满,经常被其他氏族的人接近。他的两个儿子 Dyuminme 和 Tubyaku 也成为了巫师。八十年代,极地探险家来到图比亚克,在整个苏联北部进行了过渡。他们发现老人在电视上观看飞船发射。 “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铁带入太空?”图比亚库一边问道,一边满脸怜惜地看着极地探险者们。 “我在没有铁的情况下去过月球两次......”
三十年代初期,苏维埃政权来到了泰米尔。她被飞行员带上了翅膀 - 征服北方的浪漫主义者:“战斗和寻找,寻找而不是放弃......”他们几乎没有想到他们已经给整个文化带来了死亡。泰米尔的老人仍然惊恐地谈论着某个带着地球仪的女人热情地开导了“黑暗民族”。 “孩子们快躲起来,圆石魔女来了!” - 他们当时说,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教育家和她的助手把孩子们带到城里,送到寄宿学校,从驯鹿牧民的黑暗后裔中培养光明未来的模范建设者。没有孩子的母亲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顽固的酒鬼,父亲也是如此。巫师作为苏维埃政权所不具备的教义的载体,被关进了集中营。人们向我们讲述了 Leni 的叔叔兼父亲 Dyuminme 和 Tubyaku 兄弟。他们也成为萨满狩猎的受害者。
巫师死后,只有二儿子才有资格追随他的脚步。这是传统。杜霍德有很多孩子。临终时,他给了二儿子图比亚库(Tubyaku),用铁和铜锻造并在服装的不同地方缝制了助手精神的图像——萨满服装的主要元素。 “彩绘铁”——恩加纳萨人就是这样称呼这些面具的。萨满在仪式中就是针对这些灵魂的。对于萨满家族来说,没有比这些代代相传的面具更有价值的了。
虽然在他父亲去世后,另一个儿子 Dyuminme 终生都是萨满,他们的妹妹 Nobobtie 也开始成为萨满——但人们真正只承认 Tubyaka 是萨满。兄弟之间产生了嫉妒和敌意。他们每个人都只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巫师。他们尽可能地互相伤害,甚至互相写告状,因此都在集中营里。第二次在一起。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团结起来,他们互相仇恨到死。并萨满化直到最后。
我们将与 Lenya 一起前往他的“狩猎点”。瘟疫上有熊爪印。莉娜对此非常重视。他确信不会是一只普通的熊来拜访他。我们希望萨满最终能向我们展示这个仪式。所以它发生了。
Lenya“喂养”白色和黑色熊的面具。这些熊是他的萨满动物帮手。莱尼的祖父,著名的杜霍德,有潜鸟作为他的主要助手。 Tubyaku 有一只鹰和一只狼。起初在我看来,他单调的喃喃自语和击鼓声永远不会停止。已经是晚上的第二个小时了,仪式持续了四个小时。单调的节拍和宣叙调。帮助他的妻子解释说:“他与他的熊帮手的灵魂交流。他请他们来,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想来。他说服了他们并答应喂养他们。
我记得在狩猎小屋的墙上留下了很深的熊爪痕迹。去年来的熊一定有一个人那么大。就在这时,我的思绪被一声尖叫声打断了。聚集在瘟疫中的人们打破了麻木。 Lenya 开始大声说话,用完整的声音和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或者变成更微妙的乞求声调,然后突然他不再用声音说出一些短语,而是用几乎是野兽般的吼叫。然后它再次平息,大约两个多小时单调地敲击手鼓。最后,在完成 kamlat 后,他筋疲力尽地倒下了。
“去年,”萨满的一位亲戚告诉我,“我们就这样坐了一整夜,然后我们听到苔原上脚步声沙沙作响……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在瘟疫中。我们僵住了,不敢动弹……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很害怕 - 至少逃跑了,但你会逃到哪里去?现在瘟疫的笼罩消失了 - 一个男人看着我们,原来是猎人。我以噪音为向导。走了一整夜。他看着我们,看到了火和一个拿着手鼓的萨满,然后跑了……如今,你在苔原上不常看到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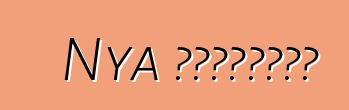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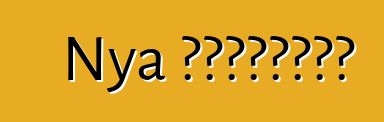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28:11 +0300 GMT
0.002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