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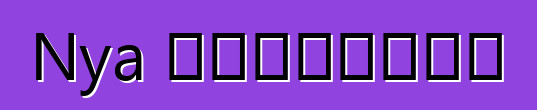



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偶然的。在杜金卡市的建築群中,彷彿是電影《潛行者》的取景地一般,隱藏著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築,上面寫著“地方歷史博物館”。在那裡我們相遇了,只是一開始我不明白這個有著東方風格的扁平臉龐的粗壯矮個子男人來這裡做什麼。他站在博物館最大的大廳中央,一個寫著“薩滿屬性”的陳列櫃前,一邊搖搖晃晃一邊小聲哼著什麼。幾人圍在他身邊,議論紛紛,男子卻沒有理會。他完全沉浸在自我中,斜眼幾乎一直都在閉著。
顯然,這是一種恍惚。然後我很驚訝地看到博物館工作人員如何恭敬地從儲藏室里為他取來一些物品,當他要一套西裝時,他們打開陳列櫃,讓他拿到存放在那裡的全套薩滿法衣。
對於我的問題,博物館館長回答說:“每年一次,他會穿著他父親的服裝來談話。”我從她那裡得知,這是泰米爾最後一位薩滿薩滿 Lenya Kosterkin,是強大薩滿家族 Ngamtusuo 的後裔。他輪流住在 Dudinka(他經常幾個月無法離開那裡),然後住在他的家鄉 Ust-Avam 村,該村位於遙遠的北部,在 Byrranga 山脈的門檻上,然後在他的狩獵“點”苔原。
他不打算成為巫師,他聽到巫師的呼喚,已經成為了一個成熟的人。他離父親還很遠,但 Ust-Avam 的居民相信莉娜身上有“力量”,有時他們會向他提出要求。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要求治療感冒、割傷、瘀傷,但有一次他幫助了一個患有某種奇怪疾病的小女孩——他們沒有向我解釋是哪一種。他被要求參加家庭假期,或者就如何“餵養”家庭偶像徵求意見。
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小時候,他的父親是如何帶他去一個狩獵點的,那是在苔原很遠的地方,他們乘坐鹿駕的橫梁(拖車)到達那裡。在所有山峰、森林和水源處,他都看到了神靈的雕像——這些地方的“主人”,它們是由他的父親,偉大的巫師圖比亞庫切割並放置在那裡的。 Lenya 和他的父親過著和所有 Nganasan 人一樣的生活:他們打獵、捕魚、放牧鹿,只有他的父親還治病救人,在苔原尋找失踪者,並安排了“初雪節”。
“人們總是去找我父親,”萊尼亞回憶道。 - 父親從不拒絕幫助。有時,在儀式結束後,chuma 會在地板上躺上幾個小時(不可能在橫樑上進行儀式)然後恢復理智,就好像被遺忘一樣。他失去了很多力量。他幫助許多人擺脫疾病,有一次他在苔原發現了一個失踪的人:他做了很長時間的 kamla,然後指出了尋找他的地方。他躺在雪下,凍僵了,但還活著。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如何和父親吵架的。然後他用斧頭砍掉了溪流中一個偶像的頭。父親甚至沒有生氣,只是奇怪地看著我,讓我把一切都處理好。我當時清醒過來,意識到我做了什麼。所以那個偶像站在我們面前,頭上纏著電工膠帶。父親原諒了我,偶像也原諒了我。很遺憾當時沒跟他好好學習。當他要給我他的主要服裝時,我拒絕了……然後他把它給了博物館。
我們乘坐一艘舊船航行到葉尼塞河下游,然後乘坐直升機飛行。 Lenya Kosterkin 和我們在一起。他需要帶孩子去城裡,他們和親戚住在村里——孩子們該上學了。
四排營房式建築位於阿瓦姆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這是Ust-Avam村。它曾經是泰米爾廣闊地區發展的前哨站。現在這裡的人實際上已經離開了他們自己的設備。 Nganasans 和 Dolgans 佔居民的大部分。村莊的北面是 Byrranga 山脈,這是一種邊疆。根據 Nganasans 的說法,在山脈之外,死亡之地開始了。在山脈的這一邊——無盡的苔原、沼澤、成群的蠓和成堆的生鏽設備。今天,只有少數家庭能夠在苔原中生存——那些沒有失去獵鹿技能的家庭。
Nganasans 不再有家養鹿 - 最後一頭在七十年代被滅絕。村里很多人家附近還停著拉著東西的雪橇。但是馴鹿永遠不會被套在這些雪橇上。老人為最後的旅程準備了雪橇和他們的傳統服裝。
1995 年至 1996 年,一群熱心的企業家在地方當局的支持下,試圖重振恩加納桑的家養鹿群。我們用直升飛機從雅庫特帶來了幾隻動物。鹿一直堅持到冬天,當天氣寒冷時,它們一隻一隻餓死了。第二次,在冬天,當葉尼塞人“崛起”時,他們試圖從河的另一邊,從涅涅茨人那裡追上鹿。在為期兩週的旅程中,幾乎整個小鹿群都去了“野人” - 一隻野鹿。 “之前,我們讓我們的鹿穿過野蠻的鹿群,我們的鹿群曾經增加了幾十頭。一家人從未離開過,”Lenya 說。我問 Ust-Avam 村的年輕人:“你們現在願意在苔原放牧鹿嗎?”通常,他們搖頭:“沒有。這太辛苦了,現在一個習慣的都沒有了。谁愿意在雪地裡睡上幾個月?但事實證明,有少數人準備回到他們祖先的事業中。 “村里的情況變得非常糟糕,”其中一位告訴我。 - 在冬天,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於是,去年冬天,我和爸爸鎖上了房子,住在離村子70公里外的一個狩獵點的樑上。如果我們有鹿,至少有一打,我們就會去漫遊了。狩獵會很好 - 我們的觀點已經完全耗盡。
曾經擁有一個巨大半島領土的人們現在在幾個小村莊繼續他們的歷史存在。恩加納桑人的數量逐年減少,現在只剩下四千人左右。或許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屆時最後一位恩加納桑的鳥魂將飛到拜蘭加嚴酷山脈之外的亡靈之地。
恰巧,來自杜金卡的老藝術家莫特米亞庫圖爾達金仍然是全民記憶的守護者。 Motemyaku 的記憶保留了 Nganasan 的生活方式——瘟疫、鹿、雪橇、薩滿……傳統的 Nganasan 生活的圖片現在只存在於他的水彩畫上。
神秘傳統的最後一位傳承人是 Lenya Kosterkin,原名 Lantemyaku Ngamtusuo。直到今天,還有關於 Ngamtusuo 部落的薩滿 Dukhod 的傳說 - Leni 的祖父。都說他能變狼,一眼就殺人。他總能找到迷失在苔原中的人,救治最絕望的病人。杜霍德作為最強的薩滿,經常被其他氏族的人接近。他的兩個兒子 Dyuminme 和 Tubyaku 也成為了巫師。八十年代,極地探險家來到圖比亞克,在整個蘇聯北部進行了過渡。他們發現老人在電視上觀看飛船發射。 “他們為什麼要把這麼多鐵帶入太空?”圖比亞庫一邊問道,一邊滿臉憐惜地看著極地探險者們。 “我在沒有鐵的情況下去過月球兩次......”
三十年代初期,蘇維埃政權來到了泰米爾。她被飛行員帶上了翅膀 - 征服北方的浪漫主義者:“戰鬥和尋找,尋找而不是放棄......”他們幾乎沒有想到他們已經給整個文化帶來了死亡。泰米爾的老人仍然驚恐地談論著某個帶著地球儀的女人熱情地開導了“黑暗民族”。 “孩子們快躲起來,圓石魔女來了!” - 他們當時說,並且有充分的理由:教育家和她的助手把孩子們帶到城裡,送到寄宿學校,從馴鹿牧民的黑暗後裔中培養光明未來的模范建設者。沒有孩子的母親很快就變成了一個頑固的酒鬼,父親也是如此。巫師作為蘇維埃政權所不具備的教義的載體,被關進了集中營。人們向我們講述了 Leni 的叔叔兼父親 Dyuminme 和 Tubyaku 兄弟。他們也成為薩滿狩獵的受害者。
巫師死後,只有二兒子才有資格追隨他的腳步。這是傳統。杜霍德有很多孩子。臨終時,他給了二兒子圖比亞庫(Tubyaku),用鐵和銅鍛造並在服裝的不同地方縫製了助手精神的圖像——薩滿服裝的主要元素。 “彩繪鐵”——恩加納薩人就是這樣稱呼這些面具的。薩滿在儀式中就是針對這些靈魂的。對於薩滿家族來說,沒有比這些代代相傳的面具更有價值的了。
雖然在他父親去世後,另一個兒子 Dyuminme 終生都是薩滿,他們的妹妹 Nobobtie 也開始成為薩滿——但人們真正只承認 Tubyaka 是薩滿。兄弟之間產生了嫉妒和敵意。他們每個人都只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巫師。他們盡可能地互相傷害,甚至互相寫告狀,因此都在集中營裡。第二次在一起。但這並沒有使他們團結起來,他們互相仇恨到死。並薩滿化直到最後。
我們將與 Lenya 一起前往他的“狩獵點”。瘟疫上有熊爪印。莉娜對此非常重視。他確信不會是一隻普通的熊來拜訪他。我們希望薩滿最終能向我們展示這個儀式。所以它發生了。
Lenya“餵養”白色和黑色熊的面具。這些熊是他的薩滿動物幫手。萊尼的祖父,著名的杜霍德,有潛鳥作為他的主要助手。 Tubyaku 有一隻鷹和一隻狼。起初在我看來,他單調的喃喃自語和擊鼓聲永遠不會停止。已經是晚上的第二個小時了,儀式持續了四個小時。單調的節拍和宣敘調。幫助他的妻子解釋說:“他與他的熊幫手的靈魂交流。他請他們來,但出於某種原因他們不想來。他說服了他們並答應餵養他們。
我記得在狩獵小屋的牆上留下了很深的熊爪痕跡。去年來的熊一定有一個人那麼大。就在這時,我的思緒被一聲尖叫聲打斷了。聚集在瘟疫中的人們打破了麻木。 Lenya 開始大聲說話,用完整的聲音和一個看不見的人說話,或者變成更微妙的乞求聲調,然後突然他不再用聲音說出一些短語,而是用幾乎是野獸般的吼叫。然後它再次平息,大約兩個多小時單調地敲擊手鼓。最後,在完成 kamlat 後,他筋疲力盡地倒下了。
“去年,”薩滿的一位親戚告訴我,“我們就這樣坐了一整夜,然後我們聽到苔原上腳步聲沙沙作響……我們所有人都在這裡,在瘟疫中。我們僵住了,不敢動彈……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我們很害怕 - 至少逃跑了,但你會逃到哪裡去?現在瘟疫的籠罩消失了 - 一個男人看著我們,原來是獵人。我以噪音為嚮導。走了一整夜。他看著我們,看到了火和一個拿著手鼓的薩滿,然後跑了……如今,你在苔原上不常看到這種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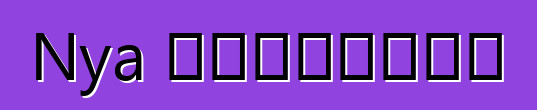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43:49 +0300 GMT
0.004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