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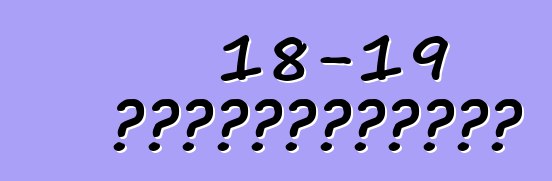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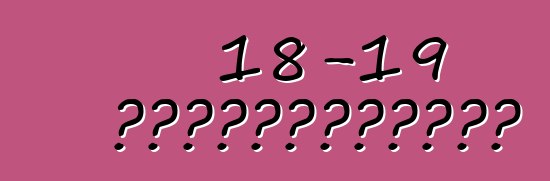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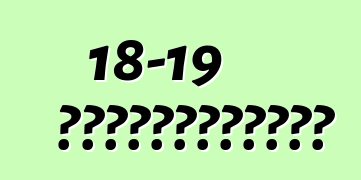
在後蘇聯地區觀察到的最有趣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是宗教協會的廣泛出現,宣稱他們的目標是實踐異教崇拜和傳播傳統信仰。在新異教組織在“原本是東正教”的俄羅斯中部蔓延的背景下,雅庫特土著居民對薩滿教感興趣似乎是很自然的,過去十年來一再宣布其複興。同時,從出版物到出版物(包括在科學文獻中),關於東正教傳教士積極鬥爭的斷言,從他們在 17 世紀出現在雅庫特開始,巫師作為傳統信仰的承載者和守護者莉娜領地的人民漫遊。在大眾的歷史意識中,消滅巫師的責任明確分配給了俄羅斯東正教會和俄羅斯殖民政府,因此今天有必要根據單獨的、零碎信息。
當然,雅庫特的精神和世俗俄羅斯當局都不能忽視巫師。除了與俄羅斯服務人員和實業家的薩滿巫師保持日常接觸外,雅庫茨克地區的州長幾乎從其成立的那一刻起(1642 年)就不得不處理一個“亞薩克外國人”對其他人的“薩滿傷害”的指控[ 1].然而,直到彼得一世關於西伯利亞人民集體洗禮的法令(1706 年、1710 年)之前,唯一直接針對薩滿教徒的措施是禁止他們在雅庫特監獄及其周邊地區信仰薩滿教:但根據薩滿教徒的信仰在鄉里,從城市到遠方”(1663)[2]。應該立即指出,這項禁令是由於一名俄羅斯軍人在儀式上被抓獲的事件造成的,而且情況加重——在四旬期!此外,這一禁令在 1696 年雅庫特州長的“記憶”中得到了證實:“是的,你應該嚴密看管它,這樣他們就不會在城市周圍薩滿巫師,也不會有人去他們那裡做薩滿教” [3].觀察縣行政中心及其周圍的虔誠現象,州長們僅限於此。與此同時,東正教和巫師之間的接觸並沒有停止在“遙遠的地方”。此外,雅庫特的一位州長(A. A. Barneshlev)本人被指控在司法和行政訴訟中僱用薩滿巫師對他的對手“造成傷害”(1679 年):“......薩滿巫師 Nyacha 和他在一起,Andreika,在樓上的房間薩滿化了,在他們的土地上,薩滿巫師使用惡魔般的吸引力和魔法去海洋和寵壞人們”[4]。
彼得一世的立法法案中沒有發現消滅薩滿教徒的要求,這成為西伯利亞人民大規模洗禮的法律依據。儘管他們的嚴厲程度和直接指示的存在:“……焚燒偶像和摧毀寺廟”,並向那些違背王室意志的人“處死”,但他們都沒有談到“偶像”崇拜者的僕人[ 5].至於鎮壓:拿走手鼓,燒掉薩滿的衣服等等,18-19世紀的薩滿,即西伯利亞人民集體洗禮後,他們在兩種情況下受到懲罰:首先,如果薩滿教徒自己接受了洗禮,因此他們將受到東正教犯罪的立法約束;其次,如果新受洗的人出席了儀式,即有一種“東正教信仰的誘惑”。順便說一句,對於穆斯林來說,根據俄羅斯法律,後者可被判處死刑(議會法典 1649,第 22 段,第 24 條)。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表明一位受洗的雅庫特婦女如何邀請薩滿為自己辯護:“......安慰她生病的女兒,而不是為了任何形式的祈禱”[6]。換句話說,她在“基督教信仰”中“保持堅強”,在她看來,沒有理由受到懲罰。宗教會議在審查薩滿教案件時,結合上述情況,專門詢問雅庫特院長“被告是否因洗禮而開悟?”這種細微差別,經常逃避許多作者的注意,對於理解問題非常重要。
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雅庫特。與西伯利亞其他地方一樣,對新受洗的原住民進行薩滿教習俗的懲罰,即“脫離正統”,通常僅限於教會的懺悔和“沒收財產”的懺悔 - 薩滿教的屬性。俄羅斯人認為這些措施很容易,有時它們的溫和性會引起下層神職人員的不滿:“……儘管根據女王陛下的法令,它被命令寬容地懲罰那些犯有這種迷信罪的人…… .. 他們,新受洗的人,不看警告和教會的工作,而是將勇氣和嘲笑歸咎於自己……他們仍然處於以前的迷信和邪惡中”[8]。另一方面,對於薩滿來說,手鼓和服裝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物品,公開懺悔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羞辱。因此,可能是關於雅庫特傳教士殘忍行為的傳說。例如,有一個傳說記載,一位教區牧師得知當地一名薩滿(新受洗的雅庫特人)會給人們帶來傷害,就強迫他在教堂裡鞠躬。一個憤怒的薩滿化作雷霆,折斷了生長在路口的一棵巨大的孤獨雲杉,導致了牧師的死亡——“kut”——牧師的靈魂躲在樹上[9]。對無法忍受的侮辱的反應足以致命。
儘管傳教士的行動眾所周知是“殘忍的”,但仍應牢記,在雅庫特從未對薩滿祭司採取過有針對性的大規模行動。有趣的是,早在 1920-30 年就確定的薩滿教徒名單根據他自己的陳述、村委會和村委會的證明、村委會會議紀要和其他檔案文件,打字稿長達18頁,有300多個姓氏,大部分是基督教出身,這表明父母至少受過洗禮[ 10]。其中有“Dyachkovskys”、“Protodyakonovs”、“Popovs”和“Protopopovs”等巫師姓氏。鑑於雅庫特人口規模較小(根據 1926 年人口普查為 235,000)[11],以及東正教傳播基督教近 200 年的活動,如此多的薩滿巫師令人懷疑-雅庫特的革命精神權威。
薩滿教著名的“生存能力”,除了傳統社會的保守主義和異教信仰與土著居民經濟活動的密切聯繫外,是由於世俗對傳教士基督教化活動缺乏定期支持。雅庫特行政區劃。雅庫特宗教政府在 1841 年抱怨說:“......當地的民政當局以這種場面自娛自樂(犧牲 - A.N.),甚至付錢給他們(巫師 - A.N.),他們停止並剝奪了根除這種現象的力量處於精神的力量之中”[12]。大多數研究人員傾向於用財政和軍事政治利益來解釋雅庫特世俗當局的立場:要求不間斷地向君主國庫供應毛皮,迫使世俗當局保護外國人免受騷擾、虐待和一切可能損害其利益的事情yasak 的集合。特別是來自過於熱心的傳教士,他們的行為能夠在 yasak 人口中引起不滿或動盪。
大概在 17 世紀。在較小程度上,在 18 世紀,雅庫特作為俄羅斯向遠東和大陸東北部推進的前哨的戰略地位決定了保持該地區人民忠誠度的必要性,也考慮在內。
這些行動,或者更確切地說,雅庫茨克地區/地區行政當局的不作為,是從上面批准的:1740 年 9 月 11 日,e.i.v.一項法令規定:“......然而,與新受洗的外邦人有關的信仰和不履行基督教律法的此類問題根本不會持續 3 天,......但任何放縱,盡可能多地給他們看”[13]。顯然,這份長期以來決定國家機構對新受洗的“yasak 外國人”的態度的文件與西伯利亞地方當局出於相同的財政和政治考慮,因為很難懷疑 Anna Ioanovna政府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
雅庫特神職人員對巫師的態度有時也不僅僅是寬容。在十九世紀末。著名的傳教士 A. Argentov 承認:“一次訪問,薩滿會給病人帶來很多好處。我們必須同意,聰明的巫師在他們還沒有成熟到最好的時候是有用的”[14]。有一次,一名牧師生病並向一名薩滿求助,而另一名牧師在 Maslenitsa 的奧列克明斯克“唱著上帝之母”走來走去,將薩滿的手鼓放在自己身上,由兩名盛裝的薩滿陪同,他們“代表他們的行動”[15]。我們假設教區神職人員對他們的羊群的放縱,這些羊群只是被正式列為基督徒,這與他們對生命的恐懼(尤其是在基督教化的初始階段)以及牧師的物質利益密切相關鄰里關係。我們可以安全地與西伯利亞西北部的案例進行類比,當時受洗的曼西告訴旅行者他們的牧師:“它根本不關心......我們的 shaitans......他首先決定抓住我們,當我們開始敲鼓時,是的,他看到他們開始付出很少並撤退了“[16]。在傳教後期(19 世紀末 - 20 世紀初),在神職人員對薩滿教的看法中,自然科學思想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A. Argentov,I. Veniaminov 追溯以及俄羅斯東北部、遠東和俄羅斯美洲人民的其他傑出啟蒙者,他們從民族志學家的角度看待薩滿教徒。
另一方面,雅庫特的巫師也不想挑起衝突。檔案資料中沒有提到他們積極抵抗洗禮。相反,許多薩滿自願受洗,甚至有一個代替去教堂用餐[17]。最後,在關於一位偉大的薩滿巫師戰勝了天花的傳說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觀點(雅庫特民間傳說的典型情節)。當 7 姐妹形式的天花精神 - 西伯利亞鶴進入偉大薩滿的 ulus 時,他“......迅速跳起來,在圖標前畫十字,化為煙霧飛向天空“[18]。評論是多餘的。
由於相對溫和的基督教化方法和雅庫特傳統信仰與基督教(至高神、生育之神等)之間明顯的相似之處,薩滿巫師沒有嚴格反對正統信仰。在這種情況下,異教意識的特點——不衝突和接受——決定了薩哈神話對三位一體、上帝之母和基督教聖徒的快速“同化”,從而導致混合主義和雙重信仰,這已被更多人注意到研究人員不止一次。
因此,“鬥爭”一詞並不能表達雅庫特教會與巫師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對巫師的直接鎮壓、暴力、迫害和破壞並沒有發生在整個研究期間,這既是因為中央和地方世俗當局的任命,也是因為神職人員本身的模糊立場。反過來,巫師並沒有特別抵抗洗禮,被認為是東正教徒,繼續他們的薩滿教習俗,在雅庫特與東正教神職人員和平共處了近兩個世紀,直到蘇聯政府著手根除“迷信”。
注意事項:
17 世紀的雅庫特(隨筆)。雅庫茨克,1953 年,第 178–179 頁
引用。引自:Tokarev S.A. 17 世紀雅庫特人的薩滿教。 // SE。 1938. No. 2. P.102
同上,第 103 頁
DAI T. 8. S. 244
西伯利亞歷史的紀念碑。第 1 卷,第 240-242 頁。
在 RS(Y) 上,f。 225,同前。 2. 文件 946,l。一
在 RS(Y) 上,f。 225,同前。 2. 文件 135. 頁 4–5
TF 加托,f。 156, 1758, d. 98, l. 2轉。
雅庫特人的歷史傳說和故事。第 2 部分。M.-L.,1960。S.261–264。
Vasilieva N. D. 雅庫特薩滿教 1920-1930 年代。雅庫茨克,2000 年,第 124-141 頁
Ignatieva V. B. 雅庫特人口的國家構成。雅庫茨克,1994 年,第 33 頁
在 RS(Y) 上,f。 225,同前。 2,d.153,l。 6rev.–7
PSZ。 T. 11. 聖彼得堡, 1830 S. 250
Chikachev A.G. 俄羅斯老前輩的薩滿療法 // 寬容。雅庫茨克,1994 年,第 99-100 頁
Ovchinnikov M. 在我的記憶中//生活的古代。 1912. No. 11. S. 855–879
諾西洛夫 K.D.在 Voguls。 SPb。 1906.
NA RS(Y),f.185,同前。 1,d.20,l。一
雅庫特人的歷史傳說和故事...... S.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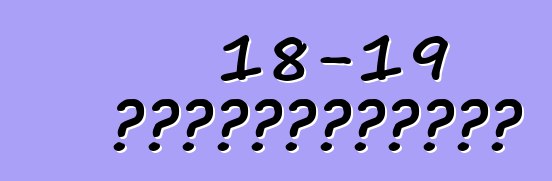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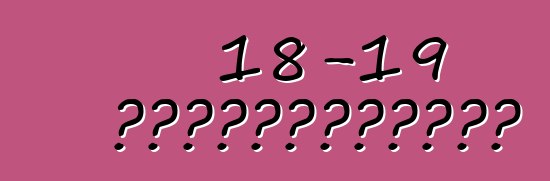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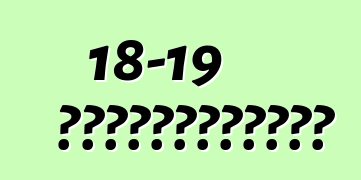
Home | Articles
April 27, 2025 00:54:54 +0300 GMT
0.010 sec.